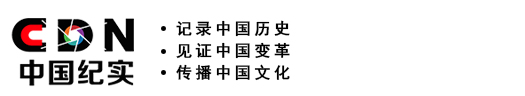红楼讲堂
否定群雄解红楼之宝玉何许人也
1.在书中塑造宝玉的目的就是作者的主题论。书中代表宝玉性质的称谓有许多种,如贾宝玉、甄宝玉、通灵宝玉、公子宝玉,还有怡红公子宝玉、混世魔王、无事忙、富贵闲人等等。现只论前三个名称,余者随文而论。 (1)从本质而论,“贾宝玉、甄宝玉、通灵宝玉”三个称谓的含义是相同的,都是代表真理。作者采用三种不同称谓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同艺术层次上阐明“宝玉”这一概念代表的“真理”所具有的社会、哲学和历史观念上的含义。 (2)从艺术而论,“贾宝玉”:代表理论上的宝玉,艺术上的宝玉。“甄宝玉”:代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确确实实、真正客观存在的一种事物,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真了又真”的事实。“通灵宝玉”:代表宝玉在艺术上的一种符号、印记和特征物。女娲炼成的这种“石头”又是宇宙和世界发展过程中最古老的象征物,以示作者阐述的真理之悠远和具有天地之理的性质。作者巧妙地运用这三种概念,来反映和表现艺术上的多层次性和阐述事物的种种关系。艺术上这种构思和设计,主要来源于作者在哲学上的虚实相兼、有无相生、阴阳相配、千变万化的哲学天道观。从而产生了艺术上的曲若游龙、千姿百态、沟壑纵横的特点。 2.曹雪芹塑造宝玉的社会政治目的和性质有十一个方面。对于他的“混世魔王”、“毁僧谤道”、“骂世之禄蠹”等,虽也属宝玉的社会政治性质,但这些性质可归于“造劫”概念之中,故以十一个概念概之。这十一个方面是: ①“通灵”;②“补天”;③“引登彼岸”;④“造劫历世”;⑤“可继祖业”;⑥“除邪祟”;⑦“疗家疾”;⑧“知祸福”;⑨“莫失莫忘,仙寿恒昌”;⑩“专治邪思妄动之症”; “可治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险之祸”等。 (1)“通灵”——所谓“通灵”实指通向真理。让世人和读者通过对书中以“通灵宝玉”所代表的真理的认识,使思想受到启蒙和教化,从而走向作者——即和尚所指出的那个人生真谛的“彼岸”世界,所谓“借通灵说此《石头记》”就是此意。 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就是指和贾雨村称兄道弟,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如“神仙一流”的儒子:“姓甄(真),名费(废),字士隐(托言将真事隐去也。)”——这种“明礼”君子,当正面临社会处于“天塌地陷”的状态之下,精神恍惚,不知所向时,即所谓:“书房闷坐”,“手倦抛书”,“伏几少憩”,精神“朦胧”,“不辨何方”,在社会发展的偶然机遇中,和“通灵宝玉”这一真理有“一面之缘”,故使他“跳出火坑”,随和尚而去。 (2)“补天”——第一回作者所言和脂批曰: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脂曰:“补天济世,勿认真用常言。”),于大荒山(脂曰:“荒唐也。”)无稽崖(脂曰:“无稽也。”)炼成高经十二丈(脂曰:“总应十二钗。”)、方经二十四丈(脂曰:“照应副十二钗。”)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脂曰:“合周天之数。数足,偏遗我,‘不堪入选’句中透出心眼。”)只单单地剩了一块未用(脂曰:“剩了这一块,便发生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就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脂曰:“妙!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脂曰:“煅炼后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学也!”),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①所谓“补天”就是以老庄哲学来阐明济世治世之道,就是建立以大观园为模式的人类理想社会。作者为实现理想社会,在理论上有历史分析,有纲领,有批判,有哲学论述,有社会模式和手段。 ②历史分析和哲学理论的阐述:从秦法、秦之太虚说起,到大观园初建,到探李钗三位一体对大观园的改革的完成,这是用老庄哲学对理想社会的历史渊源、理论论述、社会模式的系统阐述。 ③对旧社会的批判:从演说荣国府开始,经过协理宁国府,祭宗词开夜宴,破除陈腐旧套等,来阐明对旧社会的批判。 ④自传说和爱情论对“补天”的错误解释:认为作者补的是反动贵族阶级之“天”,作者梦想恢复他失去的贵族阶级生活的“天堂”。周汝昌认为:“人们总以为曹雪芹……生来就厌恶仕途……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有志于做一番大事业。”蔡义江认为:“作者……说明维持封建秩序的纲纪已经败坏,自己却无力挽救清王朝终将走向崩溃。” ⑤“大荒山”——“荒唐也。”即含无人所知,无人所晓,似荒唐不经之说——作者自嘲也!犹如庄子用言放达,寓意极深,愚人不知,“不可庄语”之意。 ⑥“无稽崖”——“无稽”,无法考察之处。 ⑦“高经十二丈”——“应十二钗”:十二钗也是石头幻化而来。“方经二十四丈”——“副十二钗”也是石头幻化而来。“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然十二钗、副十二钗之外众多之人,“合周天之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乘一百倍,为三万六千五百天之数。“零一块”——多出一块。“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即此意。 ⑧“炼石补天”之说——《淮南子·览冥》:“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后以济世救民为补天。作者在此句句设喻,暗藏天机。所谓宝玉经过“煅炼”得以“通灵”,即宝玉代表的思想经过社会的磨炼和作者在理论上的提炼,尚未被世人所理解,所应用,便日夜悲哀。它在作品中经过和尚的“大展幻术”,变成“甚属可爱”、“鲜莹明洁”之美玉。实则是通过艺术的折光,“忽明忽暗,可大可小”种种艺术变幻之法,被世人所珍爱。对作者的补天之论,待大观园结束时自会水落而石出。读者须慢慢品味。
(3)“引登彼岸”——“彼岸”:佛教语。梵语是“波罗”的意思。佛教将人生分为三个境界:有生之界,曰此岸;烦恼、苦难,曰中流界;超脱生死——即涅的境界,曰彼岸。此处作者指:沿作者指明的“通灵”之真理,使人达到与现实社会不同的另一个理想世界。 (4)“造劫历世”——“劫”:佛教把天地从形成到毁灭叫做“一劫”。《法苑珠林劫量述意》:“夫劫者,盖是纪世之名,犹年号耳。”如《红楼梦》第一回:“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造劫”:制造劫难,后来比喻人们对灾难在主客观上无法逃脱的必然性。“历世”:经历世劫和灾难。书中写道:正当士隐这类儒子处于“手倦抛书”,精神“朦胧”恍惚之际,“和尚”告诉他:“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使他去经历经历”,“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是对将发生的“劫难”的一种预测、告知。“风流”是对有才华而又不羁的人士的称谓。使之加上“冤家”二字,示这些人士要干出一番出人预料而又无可奈何的事业来。 (5)“可继祖业”——可继宁、荣二祖之业。“宁荣二祖”:既不是指清王朝之世祖,也不是指作者曹家之世祖,而是指中国历史上的老庄之鼻祖。宁荣二公的替身是中国历史上尊崇老庄思想的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之子孙张道士。从汉到清朝都以张族为道家之正统,历封二品之尊。其宁荣二魂的所在处是“清虚观”。“享福人福深还祷福”是到“清虚观”张道士处为宝玉的“太虚”初建去“祷福”。“祭宗祠”时,脂曰关键是对神像“看不真切”一句(五十三回)。故宝玉梦游秦之太虚时,宁荣二公之灵说:“虽子孙众多,可继业者,惟宝玉略可望成”,即只有宝玉代表的老庄思想对社会“济世”“治世”有用。 (6)“除邪祟”——即用“通灵宝玉”代表的真理,祛除人世间腐朽而错误的思想、理论、学说、事物。 (7)“疗家疾”——此处之“家”指国家,指“金马玉堂”之典所指的“贾府”之国家(后详)。 (8)“知祸福”——老庄在祸福问题上讲因果论,即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然而不可易;是祸福之来,人所自召。”故“知祸福”:即能根据“宝玉”“通灵玉”代表的老庄思想,知道社会和事物的发展规律,并加以预测社会和事物的未来命运。 (9)“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只要坚信以“通灵玉”代表的思想,就会使事物得到一个长久的发展和生存。即所谓“永保”社会“无虞”也! (10)“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指“宝玉”“通灵玉”这种真理对社会中那些错误的思想、理论、社会观念、意识形态和事物,能纠正其错误。如贾瑞这种老儒之子子孙孙的“助纣为虐”、“图便宜”、“以公报私”、“勒索子弟们请他”、“图些银钱酒肉”;思想上的“心内膨胀”、“口中无滋味”、“眼中似醋”、“梦魂颠倒”、“满口胡话”、“惊怖异常”等等,给这种人以教化。 (11)“可治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险”等祸——指“宝玉”“通灵玉”代表的真理,有利国利民、使社会避免遭受灾难的作用。 总之,《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基本上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旁敲侧击,用生活琐事暗喻政治上的重大事物和哲理。这就是《红楼梦》艺术上的魅力和艺术家的高超和伟大之处。即所谓:“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趟。” 作者的艺术变幻之术如孙行者的七十二变。处处一语多面,“一喉二歌”。故上面这段话又可指作者在作品中追求的彼岸世界——温柔乡、白云乡、隆兴乡也!当作者说通灵玉体现的内容“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时,作者马上借石头之言警告读者:“我师何必太痴!”一个“痴”字,敲定理朝、治俗、大贤大忠不是无,而是有;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下的“有”——“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况’,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才子佳人……开口‘文君’,满篇‘子建’……终不能不涉淫滥。”这是对才子佳人之类小说的否定和批判,也证明《红楼梦》不是才子佳人之类的爱情小说。 |
相关阅读: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红楼梦》中的“意淫”概念 2016-07-21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 红楼梦》中的女儿 2016-07-21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两赋论是红楼梦人物划分之纲 2016-07-21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王蒙《永远的谜语》 2016-07-21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王蒙《写在前面的话》 2016-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