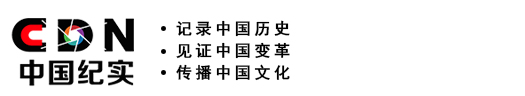红楼讲堂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红学之困”的成因》
《快读<红楼梦>王蒙评》(冯其庸) 《红楼梦学刊》(195年第四辑) 崔耀华为此而歌 宝玉可卿刚上床,名家大家齐登场; 红袖啼尽千古泪,冯王二仙托梦长。 “痛快半晌说不得”,暗皱眉头细思量。 红泪湿透鸳鸯枕 ,两株梨花压海棠。 此情世俗能醉骨,遥望红楼枉断肠。 雪芹无能作红楼,“宝玉自私无事忙”。 公子小姐穷享受,“阶级斗争总唯刚”。 二百年来终一梦,说来雪芹也荒唐。 我为二仙常叹息,沉酣一梦怎收场? 王蒙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原来又是文化部的部长,现在又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会主席,在十九岁就发表了小说《青春万岁》,可称得上是一位少年英才。近几年来他在《红楼梦》研究上出了一些书,尤其得到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高度评价。现在我就王蒙先生在山东电视台《名家论坛》上的“讲说本”、《王蒙的红楼梦》谈点看法。王蒙先生是部长级国家领导,冯其庸是中国文化部所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是副部长级的政府领导人,又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创始人、《红学会》的终身名誉会长。可以说在主流派红学界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对王蒙先生在“红学”上的高度肯定和评价是不能小觑的。而且冯其庸先生也是国家十分重视的学者。著名红学家严宽说,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曾拨给冯其庸一笔红学资金,竺琳问冯:“给你的钱花完了没有?”冯说:“我三辈子都花不完!”据说2014年文化部还奖励了冯其庸一百多万元。无论做什么,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不像我们,买支笔的钱都困难,所以我来评论王蒙和冯其庸的红学,自己都感到有点不知天有多高,海有多深。而且我亲自拜访过冯其庸先生,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学者。我拜访他时,在场的还有他对门的一位教授,我记不清了,大概叫“吴贾凤”吧!当时因为我的第一部红学《红楼探幽》刚出版,全国二十多家报纸都给予高度评价,如人民日报国内、国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信报、广州、上海、天津等等,北京日报就报道四次,而且也是开国以来到至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第一次对一个红学研究者给予报道和好评。当时是罗京播的,骆红采访的。冯其庸先生对此很不满意。他说:“我对《红楼梦》研究了几十年了,现在一些红学著作我没有必要去看,不会有什么新东西。电 他说:“他懂什么是红学,知道《红楼梦》是什么?也是不正之风。” 不过我看了上海《东方早报》、《东方网》在2013年12月5日对以冯其庸为首的红学主流派等人的批评,我觉得大家讨论一下,对《红楼梦》的研究是有好处的。我们把2013年12月12日《东方早报》周泽雄先生的文章《“红学之困”的成因》一文全文引证如下:
冯其庸先生是当代红学主流派的领军人物,是受到国家重奖的官员。王蒙先生是否在此之列,当然是,而且比冯其庸高出一个级别。冯其庸先生为什么赞颂王蒙先生的红学呢?因为二人在《红楼梦》的主题上是不谋而合,二人都属于“爱情悲剧论”。只是王蒙先生把古今中外爱情故事、爱情小说都盎括进去了,又加上自己对爱情的种种体会。说好点是对社会有感染性,说得本质些,它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蛊惑性。用王蒙先生的话说:“这可抖搂开了。”人在极兴时,会有极大的想象能力。有如:汉武帝从大月氏得大宛马,兴而作歌,饮酒二斗,夜大 兴,二妃由此得奇趣,梦中化为“二马”,命东门京以铜铸成“铜马”,立于宫院门前,今之呼之“金马门”,以标永世。 王蒙先生这“一抖搂”,对《红楼梦》在解读上和用词上就有些頗偏。如他在山东电视台讲座时第四讲:《贾宝玉的性启蒙》中是这样论述的: 他说宝玉,“他是在侄媳妇,美丽聪慧,袅娜纤巧,温柔和平的秦可卿的卧室里进行的,是在秦氏床上进行的。……本身就令人心跳头眩、甜丝丝、亲蜜蜜、软绵绵、舒服服的。 这样文艺化的性教育充满了女性的美丽,充满了语言的美化。什么叫文化?……同样一件事,以粗话脏话表达之则粗而脏,以经过修辞的美言诗句表达之则感觉迴异。男女之事,可称为‘ 操×’、‘顶入’、‘配种’、‘干’、‘偷情’、‘睡觉’、‘巫山云雨’、‘颠鸾倒凤’、‘恩爱’、‘轻薄玩弄’、‘糟蹋’、‘一夜情’… 王蒙又说: “‘仙袂乍飘’(近似解裤带腰带的修辞)、‘靥笑春桃’‘榴齿含香’(有欲吻的修辞含意)、‘花容月貌’(脸蛋儿的修辞)、‘一缕幽香’‘群芳髓’(鼻子嗅觉的修辞化,西方生理学者认为男女互相吸引中嗅觉作用最大)、‘风月情浓’(性吸引的修辞)、‘柔情缱倦’‘软语温存’(做爱的修辞)……如此这般,……是人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性生活的一大进展。与一个毫无性审美情趣的人做爱,与跟一头驴子做爱有什么区别?……那些在爱情与事业上不怎么如意的读者们啊,多读小说吧,尤其多读几遍《红楼梦》吧……” 我们说,王蒙先生说话坦诚直白,很有风趣。但王蒙先生对《红楼梦》的解读仍然是隔岸观花,梦中作乐。仍然是不辨其真伪。 贾瑞就是因为“正照风月宝鉴”而丧了命。现在的刘心武先生何止只是“正照风月宝鉴”呀?他更是“红袖添香夜读书”,一边想着秦可卿赤条条地骑在贾珍身上,一边读《红楼梦》。这样不丧命才是怪事呢! 我们说过,从《红楼梦》的“经书说”去解读《红楼梦》,书中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 艺术研究院的冯其庸先生,在1995年《红楼梦学刊》上载文大呼:《快读<红楼梦>王蒙评》一文说:对王蒙的论述,读了“痛快、解气、够味”,“一下被他抓住了,半晌让你说不得”。王蒙先生和冯其庸先生可以说是同床共枕了! 文学家的想象力是很强的。王蒙先生一共用了十二个有关两性关系的词,可谓是插花弄柳,风吹花舞;巫山云雨枉断肠,可怜飞燕倚新妆了;连现代风流女子的三点式都是多余的了。王先生对宝玉和秦氏这一节,在男女两性关系上一共总结了十二种方式和用词,有的话甚至只有在夫妻做爱时、处于高潮时才可能说的话,让人难于启齿。在后面分析时,我们会来个大扫除。对冯其庸先生,我们也要撒点除虫剂。 我要是没记错,王蒙先生已经八十二岁了。冯其庸先生好像年岁更大一些。白居易八十二岁时还娶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小妾,他的朋友赞叹他老枝横发写了一首诗: 二八少妇八二郎,二人携手入洞房。 锦水湿透鸳鸯被,一株梨花压海棠。 白居易一生风流倜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本文章已经过作者授权,未经许可不得私自转载。)(本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
||||||||
相关阅读: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红楼梦》中的“意淫”概念 2016-07-21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 红楼梦》中的女儿 2016-07-21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两赋论是红楼梦人物划分之纲 2016-07-21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王蒙《永远的谜语》 2016-07-21
·与《王蒙的红楼梦》商榷 —— 王蒙《写在前面的话》 2016-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