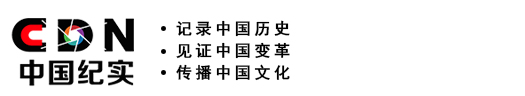黄亚洲专栏
春风化雨,在“亚洲书院”听讲文学
春风化雨,在“亚洲书院”听讲文学 作者:阮景巍
虽然读过不少诗,但对于真正的诗人,内心还是充满神秘感和神圣感的,宛若仰对夜空中的星。直到今年春天,才有幸见到了人生中第一位著名诗人——黄亚洲老师。 说起这事,首先得感谢一位好友——欧阳胜老师。和欧阳老师的相识也是在春季,当时我在一家少儿杂志社做组稿编辑。那是暮春时节,杭州一家培训机构举办全国性的少儿作文大赛,我有幸随社里去做评委。欧阳老师恰巧也是评委。开始时,只了解到他是一名残疾人作家,双腿有疾,轮椅当步,不禁暗自叹惋。 但很快,我这种悲天悯人的念头便被颠覆了。首先,他是独自开车过来的,这让我十分惊讶,钦佩徒生。然后,评委发言时,他谈笑风生,言辞充满活力,让人深受感染。我当时就在想:这需要历经多少的磨难,才能练就如此的达观? 真正和他结缘,是在午饭后。因为是在三楼评选,欧阳老师上去不太方便。恰巧我在一旁,便有年长的评委看着我:“小伙子,上楼梯轮椅不好抬,你能不能背他一下?” 这当然义不容辞,我二话没说,就背他上了楼梯。没想到这无意中的一背,竟让彼此成了好友。因为同样是实在人,同样是草根,当然,更重要的是有着同样的爱好——文学。 后来,欧阳老师还一再对那次背他上楼梯的事情致谢。我连说不必客气,因为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但他跟我说,社会的现实往往是这样的:举手之劳,何乐?不为! 他列举了自己多年来生活、工作及做慈善时中遇到的各种心酸经历。这对涉世尚不够深的我,触动很大;他的身残志坚,也时刻在激励着我。我时时在想:浙江省那么多最美人物,他就是其中之一。刻苦勤奋、自强不息、豁达洒脱、热心助人……这些美好品德,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身上也未必都有。 今年三月份,欧阳老师故作神秘地邀我一起去听一位老师讲课,讲课内容便是刚刚上映的电影《狼图腾》。为此,我们还抽空去电影院看了电影,备了课。但讲课人是谁,他笑着说暂且保密。 几天后,一个“天色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周末,我们便迎着斜风细雨出发了。在路上,他才向我揭晓了谜底——讲课人是著名影视剧作家、诗人黄亚洲老师。而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黄老师的位于拱墅区的一家个人工作室——黄亚洲书院。 尽管我有心理准备,但当听到这熟悉的三个字的时候,心头还是震了一下。想到这次是去听他讲课,顿时有种小沙弥去听佛祖讲经的惶恐与不安。欧阳老师看出了我的拘谨,忙宽慰我,说黄老师虽然名气大,但人非常随和、大气,没什么架子,不用紧张。一路上,他又随口向我说起黄老师的一些事,比如他每天要冲冷水澡,15年来不曾间断过;又比如40多年来笔耕不辍,勤奋刻苦,著作等身;再比如,为人和善坦诚,作品和人品都像车窗外这春雨一样,潇潇洒洒,润泽万物。欧阳老师的话语里满是敬重与感激,在缓解了我的紧张之余,也让我对黄老师有了想象中的印象: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艺术上孜孜以求;与人为善,豁达率性,随意处润物无声。 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黄老师早早在门前迎候,身材高大,笑容满面。见了我们,忙微笑着招呼,一边快步上前帮着推轮椅,十分热情。我骤然紧绷的心瞬间松弛了,只听他赞叹地对欧阳老师说:“欧阳,我就佩服你这身体——” 其实,黄老师的身体何尝不让人佩服。他年已60多岁,可看上去远远不像,显得年轻很多,并且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我想,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是与常年与艺术为伍,人生中诗意满满;二是心态好,随和旷达,宽厚待人。 这是一次有关《狼图腾》影片的讨论课。落座的大多是“亚洲学堂”的学员,还有黄老师的好友——路过杭州的幽默可爱、率真豪迈的叶坪老师。另外,还有拱墅区的几位领导。 在座各位老师都是博闻广识、资历深厚的前辈,我作为最年轻的小辈,有幸列座聆听,真有王勃“童子何知,躬逢胜饯”的受宠若惊感。 讨论课开始,各位老师纷纷发言,结合小说,畅谈对影片的看法,有褒有贬,角度各异,气氛十分活跃。有从影片本身的壮观场面上讲的,有从狼性与人性的对比上说的,有从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角度上分析的,有从影片主题曲上阐述的,等等,各尽其详。现场更有一位老师深情朗诵了自己观看这部影片后所写的诗歌,真挚感人。 叶坪老师发言时,他回忆了自己与黄老师共同度过的“当年峥嵘岁月”。那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相对简单、纯朴的时代。那时节,适逢改革开放,在社会空前的文学热下,文学和文人都得到了人们应有的尊重。黄老师时任嘉兴地区《南湖》杂志社文学编辑,他也笑着接过叶坪老师的话头回忆说:“当年特意抽出一天,转了几趟车,不辞辛劳地辗转几个城镇,就是想与一位投稿的陌生作者见上一面”,而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就觉得他诗文写得好。” 纯朴的年代,纯洁的文学,纯真的文人——虽已过去多少年,通过两位老师的回味,仍令人“如饮醇醪,不觉自醉”,“心向往之”。 学员们讨论完毕后,黄亚洲老师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在归纳了各位学员的认识与体会后,他提出了某个更深层次的观点:这个故事其实在一个侧面,在文化的深处反映了民族之间的统治与征服,这种互相的征服客观上构成了历史与现实世界——这是讨论时大家都没有提到的。很快,黄老师又借此谈起了文学创作:写文章务要通过事物表象,发掘作者内心深处的东西,引申出更深层次的思想。 顿感获益匪浅之余,我不禁打心眼里为亚洲学堂的诸位男女学员感到高兴,也徒生羡慕:他们有这么一位优秀的老师! 身为著名诗人,黄老师也自然地谈起了当下的诗歌创作。他讲到诗歌作品的思想性,也讲到了对诗歌技术的不可小觑,譬如他认为“通感”这种修辞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也是重要的。通感,即打通五官的领域界限,让人体的种种感觉彼此巧妙连通,达到“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的效果,为诗句增色。 为此,他随口举了个例子:春天来了,连鸟儿的鸣叫也在返青。这句诗中“返青”一词原本指的是春天的草木,却自然地运用在鸟儿的身上,显出了浓郁的诗意,给人遐想的空间。 听到这里,我联想到古人一些运用这种修辞手法的诗句,如“风随柳转声皆绿”、“大珠小珠落玉盘”、“鸟抛软语丸丸落”、“促织声尖尖似针”等等,当时读的时候就感觉奇妙无比,感叹诗人是如何想出来的。以前年幼,不能完全领略这种修辞的妙处,听了黄老师的解读,恍若记起了弃置多年的宝贝,想以后诗文中倘能适当运用一些这样的修辞,定能有所补益。当然,这宝贝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一样,须先知晓其中的秘诀,运用才能得心应手。 几个月前,一首名为《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火爆网络,在全国掀起了一股“余秀华热”。当时在微信里读到这首诗时,觉得很过瘾,但除了感觉语言大胆新奇,却又说不出到底好在哪里。那天,也有幸听到了黄老师的简单解读。他说,这首诗之所以算是好诗,除了它的语言,还因为有它的较为深刻的思想性,比如诗句中提到的“流民”“政治犯”以及撞在枪口上的“麋鹿”、“丹顶鹤”等等,都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现实,虽说是“顺便”提及,但其实作者在此赋予了深意,以此作为“苟且爱情”的必备背景,读起来顿然让人产生了对特定“爱情”的理解,从而产生共鸣。 经如此解读,一时间恍然大悟,就着那首诗再细细一琢磨,的确如此。 时间就在黄亚洲老师专业而愉快的讲解中一点一点过去,转眼已到中午,讨论课要结束了,但尚觉意犹未尽,因为分分秒秒都是收获,尤其对见少识浅的我而言。最终,叶坪老师用优美动听的演唱为我们这次活动完美地划上了句点。叶老师虽已年逾古稀,但风采依旧,倾情献唱,豪迈动人。 午饭过后,我们与黄亚洲老师及各位在场的老师道别。此时,小雨依旧,宛如言情小说里痴男怨女的相思,幽幽袅袅个不停。但看到春花含苞、草色更新的景象,我想,这应该就是“润物细无声”吧。而在亚洲书院,黄老师也洒下了一帘一帘这样的“雨”。 时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忽然暮春已至。望着窗外一幕幕逐渐长大的雨,总能想起那天听课时的情形,想起黄老师,想起欧阳老师,想起各位在讨论课上侃侃而谈的老师,如同回想暖暖春日里西湖边上的一袭袭风景,始终给人美好的感觉。 诚然,如同春天,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但记忆可以永恒。 |
相关阅读: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8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7
·这位四川总督,是个清官! 2022-01-19
·泉州的一个民俗浓郁的小渔村! 2022-01-17
·【欣赏】黄亚洲:凡人故事(外三首) 202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