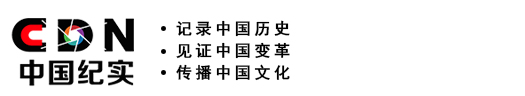黄亚洲专栏
答《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编者访谈
1983年在浙江普陀山 答《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编者访谈 黄亚洲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部分认同。就诗人的高歌低吟而言,基本上是不受时代限制的。愤怒可以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可以幸;鸟语花香的年代也可以出诗人,小桥流水也是迷人的景致。我认为,生活本身的厚度远远超过诗人歌喉的幅度。当然,由于精神桎梏的松绑,那个年代诗歌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是相当可观的。我们说的“黄金时代”,主要是针对受众而言。就受众的广度来说,八十年代当然远超现在。那时候鲜有影视更无网络,人们的兴趣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文学青年”尤其是诗人特别受宠,把头发养得长长的走在街上那是一种范儿。那年头的大学生文学社与诗社也特别火,在大学里不参加一个诗社去活动活动好像智商有些问题似的。 问:您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您自己投身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 我是1983年就读杭州大学干部专修科的,在这之前,是浙江嘉兴地区文学刊物《南湖》的诗歌、散文编辑,干了四年,那会儿就猛烈地接触到了嘉兴师范专科学校的大学生那种写诗热情。来稿真是很多,他们有个远方诗社,沈泽宜老师是其中主要的撑旗者。我还作为编辑去他们学校讲过诗歌创作,坐了满满一礼堂,人头攒动,远不止一个中文系诗社的人数。我因为1972年就以一个“兵团战士”的身份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诗作,当时已经很有一点“老诗人”作派,又身兼刊物编辑,所以到处“好为人师”,这个臭脾性到现在都还未痊愈。总之,感觉那时候的诗歌确是汹涌澎湃,那时候的年轻人不玩微信就玩诗歌。可以说,现在我们浙江的知名诗人柯平、伊甸、邹汉明、晓弦、应忆航、诸汉江等等,都是从那份《南湖》里走出来的,铅字排列作品的愉快应该是他们诗歌旅途的加速度。我1983年进杭州大学“镀金”之后,也应邀参加了杭大中文系的“我们”文学社与“晨钟”诗社,经常看见大学生们以激烈的手势与“舍我其谁”的气概谈论诗歌,尤其是借鉴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手筋”来丰富中国新诗的表现力。我觉得,在审美形式探索方面大学生们做得很冲动也做得很好,当然也包括某些诗作“朦胧”得无边无际。记得这一状况也引起了我们这些“干部大学生”(我称之为“太学生”)的善意嘲笑,我们寝室的“老大”周时奋曾经做过一个游戏,他把一大群名词一大群动词一大群介词做成纸团“搓麻将”,例如当时的诗歌热词“教堂”“钟声”“麦穗”等等全在内,然后随机排列。这样的一首首诗歌“制作”成功之后,马上叫来同楼的本科大学生“鉴赏新作”,惹得那些才华横溢的大学生捧起诗作惊呼“你们写得真棒”,直乐得大家不行。那天我是很迟才从杭州的父母家回到学生寝室的,一进门就要求我评价一首又一首的“新作”,我左看右看觉得不知所云,于是实话告知这些作品有“狗屁不通”之嫌,幸亏我的实事求是态度救了我,不然我这个多年的诗歌编辑也要被大家笑成一团了。我举这例子不是抨击那时候的诗作不好,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大学生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几乎疯魔的探索精神。说到这里,我要顺便对我们寝室的那位“周老大”表示诚挚的哀悼之意,祝早走的他能在天堂能拥有真正的诗一样的心情。人间的确没有更多诗情。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 我们是太学生》很有影响,能否谈谈这首诗? 那是在开学典礼上低头临时写就,表达的是上了年纪的大学生的不容易,他们的艰难以及他们的喜悦,后来就发表在省报上,后来收入《大学生诗选》,一时激起了很多跟我们这伙人类似的“太学生”的共鸣。也不说怨谁,就是因为时代的畸形造成了状况的怪异。我们这一代人有幸碰上了社会的种种,虽不如人意,但从“经历是财富”这个角度来考察人生,也不亏了这辈子。 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 当时没有手机,当然靠写信。记得就诗歌创作而言,跟复旦大学诗社的社长小周就有比较密切的通信来往,我很想知道上海的诗歌现状,他们比较前沿。小周是嘉兴桐乡县人,八十年代后期在没有上大学前,就参加过我们地方的诗歌活动。当时我在嘉兴市主编文学刊物《烟雨楼》,常举办诗会。小周后来从复旦毕业后调浙师大任教,也是那里的诗歌领袖。浙南温州的《文学青年》诗歌编辑叶坪,也是一个善于通过密密麻麻的信函来叙述一切的诗人,我们在八十年代也通过许多信件,至今他仍在写信,照旧密密麻麻,几乎每个月都要来一封,他长我几岁仍口称“亚洲兄”,尽管他又有手机又有微信,但似乎不喜欢空中无影无踪的电波,他改不了深夜灯下摊开信笺码字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至于“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的故事吗”,这一点与我似乎没有明显的关系,那时候我已经有家室了,再说我那时候比较严肃,一本正经的“嘉兴作协主席”派头,几乎没有感觉到“文学女青年”的过分热情。当然,我也多少了解在诗歌创作活动中发生的种种趣事,据说有人因为诗歌喜结良缘,包括后来的分道扬镳。某个诗会组织下来,事后传出发生了好几对缘分,“黄老师你当时到底有没有察觉到啊?”当时确实没有,后来有几个爱开玩笑的人由于我的辛辛苦苦组织诗会而把我这个“《烟雨楼》主”称为“烟花楼主”,听了真叫人有点郁闷。但是,当年诗歌的热像与社会魅力,由此也可见一斑。爱情借由诗生,没有什么不好的,当然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不是苟且。自然,“苟且”也要分情况,只要不影响他人,也不至于叫人反感。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那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松绑了,艺术技巧也多元了,年轻人在诗歌中激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文艺复兴”的影子。我的评价是很正面的。有的先锋诗人过于强调形式,走点歪路,也是可以理解的,探路者谁不两脚泥泞的?后来中国新诗的不断壮大与成熟,与八十年代诗情洋溢的大学生有着直接的关系。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让诗歌理论家去划界与编号吧,我作为诗人说不明白应该贴什么标签。其实把“朦胧诗”称作运动,我也是有点疑心的,觉得是不是有点夸张。但是理论家不这么说也难为他们了,他们有他们的活干。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介绍一二? 当年在大学我写得不多,影响也不大,至多是一部分读者知道我是一个写诗的,在一批诗歌刊物上发表过一批诗作,如此而已。因为在两年的大学生涯里,我的主要业余创作兴趣是在中篇小说的写作上,两年中发了三个中篇,其中一个上了《中篇小说选刊》。还写了一些电影文学剧本,当时甚至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辑鲍老师特意跑来杭州,找到杭大,守在某个教室门口见我约稿,直教我激动了半天。在我赴八一厂改稿时,知道鲍老师竟是我敬重的著名剧作家陆柱国副厂长的夫人,而且陆柱国老师后来还恳切地询问我是否有意愿调八一厂创作组,这更是让我激动。最后,毕竟是我这个小里小气的南方人没出息,想想还是从嘉兴调回山青水秀的杭州过小日子好,要不是这样,当初下决心八十年代奔赴北方打拼,戴上领章帽徽,或许我的诗艺还会有很大的长进,成为慷慨悲歌的燕士,抽出哪一句皆是寒锋闪闪,这都是说不定的事,但历史总归无法假设。我数年前因了一部诗集《行吟长征路》得了鲁迅奖,今年又因了另一部诗集《狂风》得了首届屈原诗歌奖的银奖,这都是叫一个诗人踌躇满志的事,但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实在算不得是个优秀诗人,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诗艺探索上,都乏善可陈,不过是“中国诗歌大军”里的普通一员,这样说比较贴切,虽然我这些年是这么热爱诗歌,不曾移情,我历年来的十七部诗集齐崭崭地证明了这一点。扪心想想,写诗已有四十余年,进步有限啊,真是有些惭愧,但又想到博尔赫斯说过 “一个人到了70岁还在写诗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诗人”,这才又感到了宽心,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量化标准啊。虽则我离七十还有不少年,但我一定会努力达到这个博尔赫斯标准,做上一个“真正的诗人”,毕竟挨年份混资历的事,不是特别难为。 问: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之所以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应该说,很多诗歌报刊和文学报刊居功至伟。据您了解,哪些报刊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在您写诗的历程中,哪些报刊对您的帮助比较大? 记得我当时是在四川的《星星》、黑龙江的《诗林》、新疆的《绿风》、辽宁的《诗潮》、上海的《上海文学》上刊发诗作的,还有我们浙江自己的《东海》与《西湖》。也很感谢《诗刊》与《解放军文艺》。这些刊物都是我至今被称为“诗人”的决定性力量。没有这些刊物,我不可能从诗的第一行走到第二行。要指出的是,这些刊物的编辑老师都是以赤子之心在工作的,他们的心目中只有诗歌而没有“诗人”,这也是许多年轻诗人包括学生诗人得以大面积崛起的直接原因。感谢这些默默的我至今叫不出名字的铺路石。他们有些可能已经成了真正的铺路石。他们作为道路的一部分,是有分量的。 问: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目前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具体的说,我正在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一书,请问,您对我编著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和思路吗? 希望在评价上采取公允的态度,在夸赞与“不咋地”之间取一个平衡点。毕竟那时候国家与民众的意识形态还不是很成熟,甚至到现在也是一样,许多东西再沉淀一下才可能有一个较好的结论,所以评价以留有余地为好。
附:黄亚洲八十年代诗三首
太 阳
我的漂不白的皮肤可以作证 我们是怎样喝着太阳穿着太阳的 唱完三百六十五首进行曲 就是过了一年
那时候太阳无处不在,土地沸腾 你可以说我们整个城市 都座落在太阳上面 街巷血红,交错如同炉栅
面对太阳 我们一般都以植物的形态出现 风吹过我们的脸庞,就是吹过 向日葵的脸庞 我们整齐而划一。所有的时刻都停留在 早上八九点钟 我们相信地球是只青苹果,必须 尽快催熟
现在我们已进化为动物 啮咬一切,包括那只青苹果 我们眼睛里这些鼠类般的光泽 都不属于太阳的光谱 太阳是个遥远的记忆 我们不是羿,却把所有的太阳 都射落了
但是不感到冷,心依旧燥热 阳光从脏腑向四周散发的过程,就是 出汗的过程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完整的太阳 除了早上八九点钟,我们全天候燃烧 非常凶狠
月 亮
我的手伸过树梢,把月亮 从一片云,抱进 另一片云 夜路走累的时候 月亮的长睫毛格外温柔
面对月亮 你不能说什么都不怕 那夜,我偶然抬起脸 不经意之间,就被击穿了
唐诗宋词有一半 是关于月亮的 月亮的诗意,一千年以前 就被文人的长指甲剥净了 可是今夜 我端坐在月亮底下 只感到夹头夹脑,都是诗的大雨
我害怕月亮 在许多夜晚,月色不是水 而是泪 浑身湿透的时候 我会为月亮的纯洁放声哭泣 有许多小月亮 会从我眼眶里滚出来
只能把月亮,从一片云 抱进另一片云 而不能抱进白天 月亮之泪,以河流方式 淌过白天,进入第二个夜晚 始终无声 月亮的雨水持之以恒
总有一天,我想 我会面对没有月亮的黑夜 那时候我将把手的职能 托付给树梢 心,则被眼帘覆盖 再也无法感觉雨水和诗歌
而且那时候 我相信,月亮 也将在树梢的帮助下,成为流星
那 鹰
这是一个什么也不用思想的下午 休会半天,山风很好
抬眼,我望那鹰 那鹰是一柄黑十字玻璃刀 于滑溜溜的天空上 切过来又切过去,很自如的模样
纯净的天空一块块落下来 大的做绿湖泊 小的做白水洼 再小的,就握在我手中 握成这一杯清茶
我吹一吹茶水 有片茶叶也张开翅膀 呈铁十字模样,开始切割 杯子里的天空,鹰一般自如 这是一个什么也不用思想的下午
悠悠然我抬起眼,看见 那鹰,也变作了一片茶叶 舒展,且有些儿涩 我吹口气,那鹰便飘开去 沿着我嘴唇的方向
我一下子悟及,我是更厉害的鹰 我的嘴唇是两爿暗红的翅膀 缓慢,却更凌利
起风了,四山冷下来 围成铁色的茶杯。鹰消失了 也许,它已像茶叶一样落到杯底 我的心也象鹰一样沉落 只有涩味还在 我望望山的边沿 看看有没有暗红的嘴唇临近 有谁来辍饮我呢?
这是一个 不由人不思想的下午 这时候有人来了,通知说 又要开会
载自黄亚洲诗集《无病呻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八十年代初就文学创作问题请教文坛前辈顾锡东先生
左起:黄亚洲、汤优烈、朱瑞成干事 |
相关阅读: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8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7
·这位四川总督,是个清官! 2022-01-19
·泉州的一个民俗浓郁的小渔村! 2022-01-17
·【欣赏】黄亚洲:凡人故事(外三首) 202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