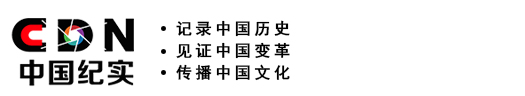历史
甲午前日本心态:中国是东亚坏朋友 会近墨者黑
核心提示: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凤凰卫视4月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894年,甲午一战,古老帝国命运骤变,不可逆转地卷入历史大潮。120年斗转星移,大国兴衰变化,世界走过战争与和平;120年国运沧桑,“甲午”二字,早已印刻在中国人的骨髓之中。两甲子的轮回,我们又站在了时代的十字路口上,中国人是谁,中国的崛起之路指向何方?身处不同时空的人们,各自寻找着答案。 陈晓楠:我是谁,是人类永恒追问的哲学命题,中国人是谁,国人亦须窥镜自视。 1894年,甲午一战,清廷的惨败重创了国人的自信。120年来一代代知识分子把反思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从“奴性”到“酱缸文化”,到“黄色文明”,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呢?而中日之间的百年纠葛,更是两个民族文化性格的冲突,或许,从东洋日本这面镜子当中,我们能够更好地看见自己,也看见未来。 李鸿章: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解说:大清国风雨飘摇之际,老臣李鸿章率先感受到了变局与危机,然而像李鸿章这样的中国人只是少数,对于外面的世界,满清皇帝与他的臣民,依旧保持着钝感。直到甲午一战,天朝大国败给了区区小国日本,中国人才真正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羞辱式的,中国人输的连内裤都没有了,这样一场战争,当然肯定很震惊。士大夫的全面觉醒,真正的害怕了。 解说:甲午之后,思潮涌动,维新的时代开始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第一个学习的对象,正是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邻岛国日本。茶道、和服、和室,对于中国人来说似曾相识,仿佛梦回唐朝。 汤重南(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日本在东亚是一个角,所有的风,各种各样的风,把大陆的、中亚的、西方的,吹到这的时候它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一层一层积淀在那,所以说中国已经失传的东西,在日本却有。 刘建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的所有的文化现象,其实都可以在日本找到痕迹,但是只有两样找不到,一个就是科举制度,一个就是妇女的这种缠足。 依田熹家(日本早稲田大学名誉教授):在外国文化大量进入中国时,经常听到“文化侵略”的论调,而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文化侵略”这个词更难以理解。因为如果将外国文化,大量进入本国称为“文化侵略”,那么日本从始至今一直都处于被“文化侵略”的状态。 解说:1868年,明治天皇号召臣民上下一心,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在文明开化的政策之下,日本集体转身向西,如海绵般汲取西方文明。 依田熹家:文明开化与中国洋务运动处于同一时期,日本不仅引进外国的机械船舶,还引进了外国的文学、哲学,涉及范围广,具有综合性。 汤重南:首先是教育,把日本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提高到非常快,它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时候,它的教育可以这么说,达到了99%的那种普及率,就是日本没有文盲了。 解说:彼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这样一个冉冉升起的日本,心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刘建辉:中日甲午之后,在中国,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自卑,用现在的话就是一种自虐史观,他们认为中国都不行了,什么都不行,日本什么都行。 解说:甲午战败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派遣公费留学生。到了20世纪初,更有大批自费学生东渡,留学日本成为潮流,鲁迅、王国维、黄兴等人均在其列,这批人成为了20世纪中国启蒙的先行者。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年代,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梁启超则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号召中国人从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 刘建辉:中国近代文化中最大的议题,就是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你看梁启超当时所有的这种对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都是出自日本对中国的批判,就可见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在甲午这个大的失败之后,他们完全可以说,对日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向往,甚至是一种学习的态度。 解说:“以强敌为师”,需要的不仅是爱国激情,更要有正视自我的理性与勇气。当时留日学生的心中,除此之外,恐怕还有些五味杂陈的滋味。 1905年,为限制革命活动,日本公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引来中国学生强烈反弹,其中一派以秋瑾和宋教仁为代表,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另一派则以汪兆铭和胡汉民为代表,主张忍辱负重继续求学。两派争吵激烈,《朝日新闻》攻击中国人缺乏团结力,是“放纵卑劣”的一群。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一个中国青年。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留下《绝命书》五千言,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尽。 陈天华《绝命书》: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即中国真亡矣。 解说:陈天华的死,并不为抗议日本,甚至不为清廷,只为“死谏”同胞。蹈海,是由岸边一步步走向深海的自杀方式,从这样漫长而痛苦的义无反顾中,仿佛可以推测出,他那内心的失望,以及对于一个民族凋零的叹息。 鲁迅1902年留日 蒋介石1906年留日 郭沫若1914年留日 周恩来1917年留日 解说:这是一个与我们如此相同,又如此不同的民族。 刘建辉:中国更多的是从构量上去看问题,比如说天高马肥,我们看季节,要看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大气在里面,但是日本它去观察一个东西,它从一个落叶,从一个非常微小的细节去感受这种东西,小的共同体意识非常强。一个很小的共同体它用不着去大声阐述自己的理论,去阐述自己的这种想法,大家很默契的就会把它做好,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我们叫暧昧的日本。 解说:恬静含蓄的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冰冷决绝的刀,是武士精神的象征。菊与刀,是美国人鲁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描述,而这个民族的种种特性,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更加微妙复杂的印象。 松村正义(前日本帝国京大学教授):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向中国学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日本的老师。因此,和老师打仗,使得一部分人内心,感到非常的愧疚。中国近代化的速度非常缓慢,而日本较早做了近代化的实践,并将它具体化,结果导致,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出现。 解说:一万元,是日本现行流通的最大面额的纸币,上面印着的人名叫福泽谕吉。 1885年,日本《时事新报》刊登了他的一篇,名为《脱亚论》的文章,正是这篇短文,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泽谕吉《脱亚论》: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脱亚论”这个思想,其实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思想,为什么呢?就是它把这个世界分成了文明和野蛮之后,这里面有非常强的,达尔文进化论的色彩。那么拥有文明的人对于野蛮的人,就有什么,就有了权力。 甲午战争,福泽谕吉他是战争的积极推动者,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什么,是文明在战胜野蛮。 解说:在文明的名义下,战争被冠以正当性,这是许多强权扩张的共性,而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支柱——天皇。 刘晓峰:传统的日本神话里面,日本是一个神国,而这个神国里面能代表这个神国的是天皇。他也成了日本,进行整个国民动员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精神资源。 解说: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之权。1926年,裕任登上皇位开启了一个充满血腥与杀戮的时代。 刘晓峰:当一个日本的军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神的国家,神国神选的子民的时候,他再看他对面的中国人或者朝鲜人他当时他就会认为他不是人。整个以天皇为中心的这种意识形态它最后在日本有一个词叫做“国体”。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的大本营也好,天皇也好,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样存续国体。它跟欧美提出来的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叫我存续国体,完了我马上就可以投降。 解说: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传》,承认自己与平民百姓一样也是人并不是神。然而在美国的支持下,走下神坛的天皇并没有为战争负责。中日之间的历史纠葛再次打上了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而在中国,满清皇帝被推翻之后国人对于自我的认同也走过了一条漫长坎坷的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东北易帜,国民党宣告全国统一。这是自清王朝覆灭以来,中国第一次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何为现代国家与国民,大多数中国人却并不清楚。 柯伟林(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到了1932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调查,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外围问人们知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大部分人知道清朝已经亡了,所以应该不叫大清国,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名字。 解说:按照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在训政阶段,要以提升国家与国民达到施行宪政的能力为目标。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了旨在教化国民的“新生活运动”。 柯伟林:教育、民族主义、国民党、共产党,教育年轻人成为中国人,国民政府确立了“国语”。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文化上将一个新国家凝聚在一起。 解说:1927年到1937年,经济进步,教育推广,被称作民国史上的“黄金十年”。但是历史留给国民政府的时间太过短暂,所有的经营与努力,都被日本的侵华粗暴打断。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历史有时候是很吊诡的,就是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可以讲在整个中国几百年来都没有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外来侵略。跟日本的这次战争,使得中国、中央政府不断地往里面撤,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断地往里面撤,因为抗日战争8年的苦难的磨炼,造成了中国相当一大批的人,虽然不是100%的,但是比以前百分之几要大多了。这个全国概念我中国是一个中国。 解说:比起甲午战争中的迅速败退,中日第二次的交手坚持了8年,最终以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一获胜而告终。战争中,中国人空前团结在了一起,然而对中国来说这场民族意识的觉醒代价毕竟惨痛了些。 日本大阪真田山陆军墓地安置着5100多名在大小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和随军人员。从1877年的西南战争一直到二战,跨度将近两个世纪。墓地的一角有六座特殊的墓碑,碑文上清晰刻着“清国”二字,这是甲午战争中被日军所俘的清军士兵之墓。 记者:这里有部分碑文被划掉,为什么会这样? 吉冈武(日本真田山陆军墓地维持会常任理事):这个地方本来写着“俘虏”,被捕后成为俘虏,在日本人的意识里成为俘虏是非常可耻的事,被认为是耻辱。即便是敌国的人去世之后,墓碑上也不能写“俘虏”二字,就把这些字去掉了。 解说:日本人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心抹去了中国人身上的“俘虏”二字。中国人却一再地将“卖国”之名扣在国人自己的身上。远有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的李鸿章,近有购买了日本汽车的同胞。 2012年,钓鱼岛问题争端再起,中国各地爆发了激烈的反日示威,中国人的愤怒,究竟从何而来。中日之间百年来的纷纷扰扰总有相似之处。 柯文(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如果追溯到1915年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的反应,你知道的,那是国耻,当时有抵制运动,游行示威,提醒人们“勿忘国耻”永远不要忘记国耻。但在几个月之内一切都平息下来了,游行示威也停止了,所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就问,我们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我们只有5分钟的愤怒,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解 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中“反日”是一个关键词。抵制日货,焚烧亲日官员的住宅,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也将“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引入了中国,被视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这些依旧与日本有关。 刘建辉:日本大正时期它主要叫做民主主义,而这里边更多的是对西方的一些价值的再诠释。比如说对人的,个我,自我的这种解释,对妇女的认识,对儿童的这种发现,都通过像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这些人他们都把这些大正的文化的精髓拿到了中国。并且在五四中得到了一个发扬。当时郭沫若说了一句话,我们留日的人占整个知识分子的70%,可见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势力。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当时是远远要超过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的。 解说:此后,中日关系走过了最坏与最好的年代,中国人复杂的民族情绪却并未随着历史的远去而变淡。 1978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打破坚冰,百无禁忌的时代。青年拥抱着萨特、尼采与弗洛伊德,人们谈理想,谈哲学,思索中国向何处去。在八十年代进入尾声的时候,爱国主义教育蔚然兴起。 柯文:为什么需要爱国主义教育,因为中国出现了信仰价值的真空。中国人相信什么呢,中国的年轻人被灌输一种中国已经忍受很多年耻辱的观念。但这些年轻人与他们的长辈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但这些年轻人没经历过。所以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愤青”的原因之一。他们并没有对这些东西深信不疑,但他们又认为这是正确的事。 解说:经历了长期的压迫与侵略,从集体主义中走来的中国人是继续背负耻辱与愤懑,还是以大国国民的自信前行,这或许是在当今中国一个难以避开的选择。 柯文:我认为中国需要感受到它是被其他国家所尊重的,被视为一个大国。我认为现在是这样的,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越长,残留的“国耻”感就会越少,直到人们都注意不到它。 陈晓楠: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他在那个不堪的年代里,为唤醒国人自信而发出的呼喊。如今的中国人,已经很难说是没有自信,但为什么我们总被视为是敏感而又易怒的一群呢。在物质生活上已经充分适应现代化的中国人如何在精神上也能做一个爱自由、讲公德,既独立又合群的现代人,或许还有一段路要走。明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中国崛起之路上,大国之间的碰撞与交锋。 |
相关阅读:
·探秘汉文帝陵——何为霸陵 为何霸陵 2021-12-16
·陕西发现汉文帝陵墓 2021-12-15
·新“丝路人”的精神图谱——记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创 2021-12-14
·不忘·回响 2021-12-13
·陕西咸阳发掘3600多座古墓葬 2021-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