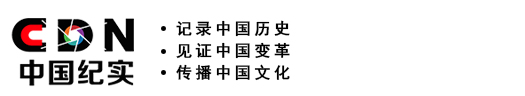黄亚洲专栏
我与亚洲老师的文学之缘
我与亚洲老师的文学之缘 作者:王 立
我与亚洲老师的文学之缘,应该上溯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1980年,我从乡村进入濮院小学的校办工厂工作时,才16周岁,正是名副其实的青少年时代。工作之余,有漫长的业余时间,好在我打小就喜欢上了阅读,尽管只是小学毕业,囫囵吞枣的阅读久了,就放不开这个爱好了,而且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居然生长出了写作的梦想。 正值青春年少,又有大把的时间与精力,业余爱好当然可以还有其他的选择,如与同事们一起打扑克、搓麻将这种最普遍、也最轻松的娱乐活动,或者抽烟喝酒聊天吹牛皮,然而这些事情我偏偏都不喜欢,那么就只有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当时,我的交际范围也就仅限于工厂里的十来个同事。文学这个爱好,没有人同行。 我居住的工厂宿舍,窗外是老镇居民张家的院子,天气炎热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吃风凉夜饭,乘凉聊天,而我就在灯影里蚊子的侵袭下捧卷读书,或者在稿纸上涂涂写写。时间一长,他们知道我在写作了。大约是两三年后的某一天傍晚,张家大哥凑到我的窗前来说,昨晚他们去看了一部电影《R4之谜》,是兵团丝厂黄亚洲写的剧本,不过他已调走了。他还说,你好好写,以后也写部电影出来。当时我突然很激动,原来作家曾经离我这么近! 从南横街的校办厂到梅泾路的兵团丝厂,就一条小巷。走过古老松动的青石板路,过了梅泾河上的桥,往前转个弯就到了,全程不到500米。然而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到校办厂上班的前一年,亚洲老师就已调往湖州的嘉兴地区《南湖》杂志社做文学编辑了。从1975年到1979年,出生在杭州的他在这个江南古镇工作、生活了五年。 那天晚上,我连书也看不下去了,熄了灯躺在床上,听着屋后小巷中有人走过青石板路时发出的咯噔咯噔的声音,睁了眼睛看向无边的黑暗,想着有关文学的心事。也就是从那时起,记住了一个作家的名字:黄亚洲。 当然,那个时候,我仅仅是在练习写作,万万不敢把连习作都称不上的稿子寄给《南湖》杂志的编辑黄亚洲。 1985年4月,濮院镇文化站新来了文化干部周敬文,一到濮院,他就走访、联系了濮院的文学爱好者,并成立了梅泾文学社。 也就是这一年,亚洲老师从杭州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毕业,调到了嘉兴市文联工作。他创办了《烟雨楼》文学杂志,随后又担任了嘉兴市首届作家协会的主席。后来知道,他是被在湖州的嘉兴地区推荐去杭大读干部班的,而他读书期间,湖州嘉兴分设为两个市,这样他就被分配到嘉兴了。嘉兴市的文学工作也在一个新的节点上开始了发育。 在梅泾文学社中,周敬文是我们大家都视如兄长的人。他是个杭州知青,喜欢文学,应该与亚洲老师早就相识,所以在文学社成立后的第二年,他居然把《烟雨楼》主编黄亚洲、编辑朱樵请来了濮院,假座兵团丝厂的会议室(当时该厂文学爱好者众多,如赵国平、王兴发、王亚平、董君莲等),为文学社的社员讲课、指导。然而,如此盛事我却没有赶上,因为我去外地出差了三天。等回到濮院,去了文化站,听周敬文讲述了这场文学活动之后,心中是满满的遗憾与失落。 慕名多年的亚洲老师来了濮院,而我居然错过了相识的机会。 1987年,亚洲老师前来濮院访友。因为周敬文事先告知了我,我终于在文化站见到了亚洲老师,高高的个子,朴实而又温和,仿如邻家的叔叔。我向他汇报了自己的创作现状,当时我仅发表过十余篇作品,有散文,有小小说,还有两首短诗,而我的目标是想写小说。其实,我对自己的写作方向在那一时期是非常模糊不定的。亚洲老师听了以后,认为我不一定要挤在小说这条羊肠小道上,建议我是否考虑向评论方向发展。亚洲老师回到嘉兴后,还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再次鼓动我:“评论这条路,不妨认真走一遭。” 主编《烟雨楼》的亚洲老师还寄来一篇韦蔚的小说处女作,约我写一篇评论。我知道,这是亚洲老师给我一个锻炼的机会,心中自是感激而又珍惜。这篇发表在1988年第2期《烟雨楼》上的《匣子里的挽歌》,便是我的“评论”处女作。 应该说,这么多年来,我写了大量的阅读随笔,是与亚洲老师1987年对我的那次鼓励分不开的。但是,我的文学基础差,理论水平低,对于真正的文学评论,始终望而生畏,更无法往高处走,实有负亚洲老师的期望。 而且,我的业余写作依然很杂。诗歌是彻底放弃了,散文、随笔、小说一直在写,没有系统也没有重点,所以也就无法获得更大的突破。有时候想想,在社会基层做一个真正的、纯粹的阅读者、文学爱好者,也是很美好的事情。至少,我的精神世界因为文学而丰饶、而多彩。 电影《R4之谜》到底没有看过,但是后来看了亚洲老师编剧的《观音今年十二岁》《开天辟地》《日出东方》《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影视剧,并且经常看到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诗歌,当然还有小说,对《交叉口》《礼拜天的礼拜》等小说也记忆犹新。 亚洲老师自从九十年代初调往杭州后,职务不断往上升迁,如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作协主席,还兼任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自然还担任了更多的社会职务与荣誉职务。我知道,这些职务的背后是大量的公务活动,肯定要占去他大多数的日常时间,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创作出一部又一部新的作品。他的时间与常人一样多,每天24小时,除了公务活动、吃饭睡觉这些必须支出的时间以外,完全要靠挤时间来创作。这里面,才华、决心、毅力,一样不能少,还有体力;这个属牛的作家,真的拥有牛一般的犟劲,从容地调和了工作、生活与写作之间的矛盾。 文坛上的劳模之称,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文坛中人看来,亚洲老师有一枚标签是“主旋律作家”:写电影《开天辟地》,写长篇《建党伟业》,写诗集《行吟长征路》,写长篇《雷锋》,写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片“红色”。我知道,很多作家是不屑于涉及“主旋律”题材的,似乎这样浪费了他们的才华,或者影响了他们的品质。事实上,艺术的高与低、雅与俗,与什么“旋律”是无关的。 在任何时代,人心都需要正能量文艺作品的滋养与激励。关键在于作家的立场与担当。关键是作品呈现的真诚度。 曾经读到亚洲老师的一组随笔,在长达数万字的篇幅里,主角是“访民”刘凡恩,还是一个顽固的“京访”。老刘是一个退伍老兵,然而阴错阳差,造化弄人,他居然“被丢失”了户口,没有了身份,这意味着他不能合法地获得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一切政治权益与生活保障。青年刘凡恩从26岁开始进京上访,给历代最高领导人都写过申诉信,但是,经历了51年的漫长上访,居然没有一级政府或一个部门能够切实地帮助他找回失去的自己,就这样一直到了77岁,老刘在走到人生终点时,还没有获得一个应该有的合法身份。然而,亚洲老师关注到了这个夜夜躺在北京西城区西什库大街与大红罗厂街交叉口的那道半圆形屋檐下的老刘,从2010年11月19日到2014年5月13日,他以手中的笔不断地为老刘鼓与呼——这在某些官员眼里,亚洲老师做法或许是“不合时宜”,有违“维稳原则”,因为访民一般是要强行遣送回原籍的,即使老刘没有了户籍,你一个作家又给政府添什么堵?但是,亚洲老师对访民老刘的状况追踪了将近四年时间,从偶然“抓一把糖”给路边晚年的老刘开始,为这个一无所有的老人送去了人间最后的温情与关怀。 这是一个作家良知与道义的体现。 我认为,这也属于“主旋律”范畴。 自从1987年相识亚洲老师以后,一去经年,不敢相扰。一方面深知他的繁忙,另一方面我实在没有什么“力作”可以呈请老师的。所以,27年间,鲜有联络。 其中,有过一次机会。2005年12月中旬,我前往浙江省委党校,参加了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作家协会举办的“浙江省首届文艺评论研讨班”。在为期一周的时间,主办单位邀请了七个来自京、沪、杭的老师作精彩的讲课。在这个培训班上,我见到了省内外很多文坛“大咖”,唯独没有看到身为省作协主席的亚洲老师。在培训班的最后一天,省作协的领导向大家说明情况,说亚洲书记其时正在国外访问,赶不回来。我记得这个领导称呼“亚洲书记”,这是因为亚洲老师有一个党内职务: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于我而言,潜意识中还是尽量不要轻易打扰亚洲老师的好。 然而,又得打扰他。 2014年3月,濮院镇领导决定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我与夫人合作的文史随笔《人文濮院》,这部书要在5月中旬的“中国·濮院毛针织服装博览会”上赠送给与会的全国各地来宾。因为这部稿子已经过修改、扩容,出版社原有的版式需要重新排版,重新申请书号,所以时间非常紧张,幸好出版社的周编辑在第一时间抢赶流程,一边等书号下来,一边进入出版程序。这个时候,就想起要请人做个序,主要是要起到宣传濮院、推介濮院的目的。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呢? 当然,“黄亚洲”这个名字跳了出来。 但是,我没有丝毫的把握。 3月19日,我试着给亚洲老师发了个短信,说明了情况。刚过一个小时,我就接到了回复:“请发我一个底稿。亚洲于京。”亚洲老师没有拒绝,我的心惊喜地一跳,立即就把《人文濮院》的底稿发到了他的邮箱。 当然,我还有点担心,他在北京一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担心他太忙,会拖延很长时间,如果真是这样,就会影响出版进度。 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3月26日,我收到了短信:“有邮件发送,请查收。亚洲。”赶紧登陆电子邮箱,接收了亚洲老师的序《建议你穿越濮院古镇》,于是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赶紧将这篇难得的序言发往了出版社。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亚洲老师正在北京赶写长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从剧本改写成80万字的的长篇小说,他从2013 年11月进入,必须在次年的4月底完成,以便保证在同名电视剧8月播出时能够出版。这6个月在京的创作时间,对他而言是日夜兼程加班加点的。显然,他完成的这则序言,硬是挤出时间写的。想必我约他作序这事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长篇写作,所以当时的一声“谢谢”,虽然带着感动,但还是显得轻飘了些,应该还要加上“歉疚”。 通过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亚洲老师依然是27年前那个朴实而又温和的“邻家叔叔”。
“现在,我就建议你的脚步走进书页,去踩响那条音乐般的青石板小路,建议你在运河、石桥、古屋、大树、茶肆、客栈、灯笼与绵绵细雨中品尝历史,并且在运河的越来越急骤的流速中,遐想古镇的未来。”
这是亚洲老师在《建议你穿越濮院古镇》中的一段话。诗歌般的语言,充满了深深的乡情。很多读者在读了这则序后,都由衷地表达了赞美之意。 亚洲老师在古镇生活的五年间,可能也属于他一生的“黄金时期”。诗歌的持续创作、短篇小说与“电影剧本”的尝试写作,都在这五年中发生,他理想的天空如同彩虹一样美丽;而这五年中的结婚成家,更使他尘世的温暖有了完整的诠释。他的“结婚证书”就是1978年在濮院镇人民政府领取的,据说上面还印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这是时代的烙印;甚至更据说,他那份结婚证书上按的女方手印子,是他的党委办公室的另一位姓吴的打字员姑娘,也就是说,踩着青石板路去镇政府办理结婚登记的一对男女,是“假夫妻”,原因是他的未婚妻那时在湖州三天门的另一家“兵团丝厂”担任团委书记,一时请不出假赶不来濮院,所以亚洲老师临时就“拉郎配”了,反正濮院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认不得濮院丝厂里的一千名青年男女,只认“结婚介绍信”办事,而厂里能够开介绍信的却又是黄亚洲本人,他是厂里的“党办主任”,抽屉里有党委大印与行政大印。后来听说,那位吴姓姑娘在“兵团战士聚会”中,还笑指黄亚洲说:喂,去查查结婚证书,那年是谁盖的手印子? 这又是埋伏于濮院古镇的一段悄悄的佳话了。 也显然,可以这样说,亚洲老师小说、剧本的创作事业,以及他的家庭生活,就是起步于这个京杭大运河岸畔的吴越古镇。 因此,我能感受到亚洲老师序中的文字是有温度的,并且灼热。 也正因为如此,我与亚洲老师的文学之缘,完全可以用“乡情”串联起来。我相信,这不是我的自作多情。
草于2015年9月6日 |
相关阅读: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8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7
·这位四川总督,是个清官! 2022-01-19
·泉州的一个民俗浓郁的小渔村! 2022-01-17
·【欣赏】黄亚洲:凡人故事(外三首) 202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