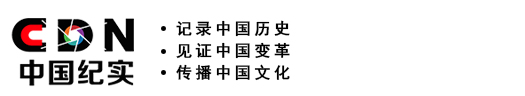黄亚洲专栏
作家在英国如此蹭饭,也是醉了!
随 笔
蹭了上帝一顿饭
黄亚洲
路过小教堂门口,转头望了一眼,只略略表示了一下好奇,便被站在门口的一个皮肤黝黑的壮汉注意了,立马朝我手势示意,意思是我可以进门。 而且那意思是,欢迎我进门,我看得出来。 我站在门口犹豫,一再朝里望。我见到的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摆放长椅供人做礼拜的大厅,已经改成一桌一桌的餐厅模样。围桌吃喝的人很多,就像是在搞什么联谊活动。 壮汉还是很客气地鼓励我进门,但我仍是犹豫,心里打鼓。 其实我是很乐意参观教堂的,那是一种文化,是人类集体思想的某种看图说话。我即兴写过欧亚美澳许多教堂的感怀诗,就是我热爱此种文化的例证。再说,这座红砖小教堂就位于我临时栖身的酒店隔壁,每天数次经过,平日都大门紧闭,如今周六下午总算开了门,进去瞧瞧也挺合适,门口的这位壮汉又是如此的客气,知道我不会英语,一再用肢体语言与我交流。但是,问题是,我吃不准里面众人用餐的含义。最简单的疑问是,白吃的,还是付钱的? 因为就在关键时刻,我瞥见了靠近大门之处的那张长桌,有一位工作人员的手边摆有一叠写有号码的票簿,可见是撕给每一位参与者的,而里面的取餐区认票,没票不能吃,问题这就来了,这票是白领的,还是要花英镑买的? 以我有限的知识判断,既然有票,大体就是要买的,不然就多此一举了,但同时也估计,教堂举办活动餐饮也简单,钱也会少收一点,成本费吧,不至于宰客。这么来回一想,干脆就免进了,花钱吃那些我们中国人吃不惯的简式西餐,譬如三明治之类,那还不如回酒店去。 所以我最终还是朝那位客气的壮汉摇摇头,用中式英语道一声“伤口”就走了。 以上说的是半个月之前的那个周六的事,说的是我究竟没有进教堂吃喝,而这会儿,偏又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傍晚时分,回酒店途中又经过了这家造型优雅的红砖小教堂,而那位壮汉又笑眯眯的出现在门口,又是那浓浓的餐食气味飘出了教堂,探门一看,果然又是一桌一桌的食客,这下我倒是有些犹豫了。 因为这半个月中,我已经听说有个别教堂会提供一种免费餐,这也算是一种文化,但也没去具体打听,免费餐是不是只提供给教友的,还是口里不说“阿门”的众生也能进门享用的,若是后者,岂不是好,得以免费吃喝,省却了我一顿晚餐,在英国也没有“八项规定”之说,哪怕民脂民膏也是他们英国人的,何乐而不为。 我本性里总有贪小便宜基因,一辈子没改掉,此刻,这种思想夹着少数唾液,顿时蠢蠢欲动。 况且,门口的壮汉似乎认出了我这个曾经犹豫过的黄种人来,比上回更见客气,笑容连着手势,一副恳请我进门的意思。 那就进去罢。 教堂外面看着不大,其实里面挺宽敞,厅堂里的餐桌少说也摆放了二三十张。用餐者男女都有,上年纪的居多,吃得热闹但基本没有声音。主食是一张卷起来的麦饼,饮料两种,有红的,有黄的。 大门边依旧是那张长桌,那一叠票簿依旧放在一个人的手边。而长桌的另半边,却摆满了红红绿绿各种蛋糕杯,像是专供进门者领取的。几十个蛋糕上的巧克力或者奶油色彩斑斓的,真是个诱人。我这人向来不忌甜食,好这一口,所以一见就倾心。桌后的工作人员见我进门,又见我瞄着蛋糕呈现出想拿又不敢拿的态势,便笑容可掬,立即示意我可以直接取蛋糕杯。我装模作样从裤兜里掏出皮夹子,做礼貌状,对方见状,急得一个劲说“孬孬”,意思明显是可以白拿白吃。 这反应,基本上在预料之中,正合眹意。 挑一张没人的小桌,坐下享用蛋糕。桌上每个餐位都备有刀叉和餐巾纸,很是周全。没想到的是,这巧克力蛋糕竟会做得这么好吃,不仅极甜,而且甜得正宗,我说的正宗是指吃不出任何的甜蜜素与防腐剂,当然国内的甜蜜素与防腐剂我也吃不出来,我只是心理作用,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会略微圆一点儿。 一小杯蛋糕原来是三口两口就可以吃完的,因为太甜,所以只能小口抿着吃。吃完之后,食欲开了,就寻思着跟众人一样,干脆在这里把主食也吃掉算了,完整地蹭上帝一顿晚饭吧,回酒店就不吃了。这么想着,就起身,大大方方走到另一头的取餐区,冲工作人员笑一笑,然后点点桌上的一卷麦饼,再点点一杯如同橘子水的黄色饮料,表示要取用。谁知工作人员不给,叽里咕噜一番,我听不懂,但意识到“票”起作用了,在这里取一份主食一定是要一张票的,怪不得门边长桌上专门有人在管票簿。 于是赶紧走回门边,老老实实掏皮夹子摸英镑,心想,蛋糕是前奏,免费的,之后就真刀真枪了。不过再想想,这也对,谁叫你沾了好处不走人,非要得寸进尺呢。 西谚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也没有免费的晚餐。 却没料到的是,管票簿的老头此刻不给票,哪怕我掏出皮夹子出示英镑也不给,也对我叽里咕噜一通。这一回,对方肢体语言再丰富我也弄不懂了。 正在尴尬时分,忽见对方连连打手势,意思是直接叫我去取餐区,明显是不用票也能拿的意思。他的手势同时打给了取餐区的人员。 我迟疑着走回取餐区,那个曾经跟我要票的人再也不说什么,只是指着两种不同馅儿的麦饼,殷勤地问我要哪一种,他那意思我是猜出来的,因为对方说话的单词里有“色拉”的读音,我明白他是在问我要放了色拉的,还是要不放色拉的。 我取了一张没有放色拉的麦饼回到座位上,像众食客一样,细心地把麦饼卷成一长条,和着橘子汁咬嚼。馅儿是鸡肉与生菜的混合,我凑合着吃,虽然不太习惯这种西式吃法,远没中餐可口,但想想教堂这么热心地对待你,两次掏皮夹子都回答“孬孬”,又给甜的,又给咸的,既有荤,又有素,还讲究啥呀,知足吧你。 期间,又见一位满面笑容的工作人员端着装满蛋糕杯的大餐盘,来回穿梭,逐桌弯腰询问还要不要再加一份甜食,殷勤得像儿子问娘似的。轮到我的桌子,我急忙摇手,不是我客气,实在是吃不下了,没想到一张麦饼会实实在在的这么胀肚子。 抹抹嘴巴,起身,看看殿堂尽头那位十字架上流血的基督,心里很感慨,你凭什么就让我蹭了这顿饭呢? 我的祖国也有仁慈的佛庙会布施腊八粥,不过那种庙宇不多,一年也只有腊八日一次,还须清晨排长队,晚了就没了。而这教堂,每礼拜六下午都来一次,一年里算下来也有五十多次,一顿实实在在的晚餐,档次也不低,尤其那甜食,放在甜品店里都是卖高价的东东,加起来也是一大笔经费啊,上帝啊你这是何苦来着。 进佛庙是我们烧香,这是上帝烧我们的香啊。 我猜想,教徒进门是凭票吃饭的,票簿撕到哪个数字就说明有多少教友来领用免费餐了,而我们这些从来不划十字不念阿门的过客,则属于见者有份了,上帝一视同仁。 这样的宗教确实是叫人心里暖洋洋的。我要是在英国住的时间够长,酒店也总在这教堂的隔壁,恐怕有朝一日也会心甘情愿的戴上十字架,这可真是难说。 关于这个小教堂,事后,我发微信,向我女儿的那位嫁在英国的幼时闺蜜作了询问,她专门查了网上资料,告诉我,这教堂的全名应该叫做“圣三一布朗普顿女王门教堂”,说这教堂可能是属于“圣公会”的,说圣公会源于天主教,是英国宗教改革的产物,是基督教中的新教的最大派别,也是英国的国教,主张各教学说的有机融通。我不怎么懂基督教里的各派别,以及他们与天主教的种种复杂渊源,我只知道是教堂,挂着的是十字架,我这顿饭是上帝给蹭的,这就够了,够感恩的了。 于是也明白,这样脾性的教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会有多么快,多么顺畅。 我的长期陷入信仰危机的同胞,见着充满温暖与同情的组织,会有多么感恩。 所以,也不必老念叨人家怎么有“亡我之心”,要想一想自己是拿什么对待自己的子民的。哪怕是加了甜蜜素与防腐剂的,也得笑容可掬地经常施予,最会感恩的其实就是百姓,尤其是中国的良民。 不过,在我,如果硬是要挑一个宗教皈依,我可能还是得挑上佛教,腊八粥的味道毕竟胜于三明治,这是肠胃的原因,没得救。 有点对不起了,“圣三一布朗普顿女王门教堂”,以及你那特别难忘的巧克力甜食。
|
相关阅读: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8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7
·这位四川总督,是个清官! 2022-01-19
·泉州的一个民俗浓郁的小渔村! 2022-01-17
·【欣赏】黄亚洲:凡人故事(外三首) 202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