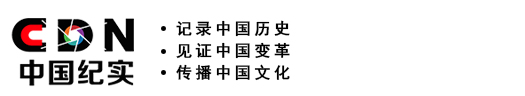黄亚洲专栏
揭秘:《雷锋》作者和亚洲书院的美好时光
还有这么一座正在讲学中的亚洲书院。有时是风起,有时是日落,有时是人潮汹涌的喧哗,有时是曲终人散的寥落,我的心头常会莫名飘过一些暖,就像天空闲闲舒卷一些云,因为一些人、一些事,比如在亚洲书院度过的美好时光。 是什么时候认识亚洲老师的?亚洲老师其实是我学长,我们共有一个倍受尊敬的老师,我用了老师的名字去亲近他、向他约稿?或者应该是更早,在他的诗里、书里、电影里,那些令人窒息的思考,或拍案叫绝的句子,那些所有共和国同龄人共有的时代良心与家国记忆。但更贴近地认识他,还是在他的书院——位于拱墅区大运河畔的黄亚洲书院。 书院,多令人神驰的地方,到长沙你会想起岳麓书院,到庐山你会想起白鹿洞书院,到武夷你会想起紫阳书院,而到杭州,自然是亚洲书院无疑。 第一次去书院,是从拱辰桥东下车后步行,很近的距离,却差点迷路。下了车右拐,就是大片的田园,正是春暖花开季,满目的姹紫嫣红扑面而来,像无数的未来引人入胜,且走且张望着探寻,就像小时候,穿过田野去看小溪水。一分钟前的车水马龙,瞬间如前世今生,后来我又几次从此下车,却如武陵人发现的“桃花源”,再如何处处志之,亦不复得路。 以亚洲老师的繁忙和惜时,他对书院却情有独钟。即使在北京闭关创作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最紧张的时候,也几乎从未中断书院的授课。是的,书院必有弟子,必有山长。必有朗朗书声和拳拳向学之心。书院的弟子不多,十几个人,是亚洲老师理想的规模,能形成讨论氛围,又不过于嘈杂。从孔子到柏拉图,到离去后我们才惊觉的木心,他们都有这样的书院情结,那些烛照历史的思想,也往往在这些书院和书院追随者心里留存、传播。 亚洲老师有很多身份,但他最珍惜的还是诗人。犹记亚洲老师讲诗,七个关键词揭开诗歌的秘密,那么透彻和浅出。一直以为,现代诗是难以进入的,但在他这里,世界是如此开放、静好,你只要走近、品读,只需一双眼、一颗心。 在出租车里写作、在飞机上帮学生改稿、在余震不断的灾区出版诗集的亚洲老师,自然没有很多时间备课,可他的每一堂课,都如此令人回味绵长。 冀汸离世,亚洲书院举办冀汸纪念诗会——七月的流星殒落,七月的精神永存。多少亲历那个时代的诗人和作家——王旭烽、薛家柱、龙彼德……一边朗诵,一边泪流。在错过的时代里,多少人生努力出彩。 当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风靡一时,亚洲书院又举行了“邓小平和我们这一代——杭大中文系83届同学会”。这些改革开放后的首届大学生,这些浙江以至全国文艺界大腕,这些已经不再年轻的精英,当年,就是他们深情地喊出了“小平,你好!” 京杭运河申遗成功,作为运河文化地标的亚洲学堂,第一时间举办大运河诗会;每年的“与民工作家共进年夜饭”,新绍兴人麦秸和杭州公交司机郭祥勤等都是座中常客……每一次大家都迢迢而来,从金华,从绍兴,从上海……因为热爱,因为亚洲老师。 有人说,亚洲老师的诗,至少有两个特质,一是永葆的童心,一是底层的关怀。其实,他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以他曾经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浙江省作协主席身份和堆积如山的创作任务,在颠簸的汽车里批阅我们这些籍籍无名者的习作,让人不由想起鲁迅的“为自己不能使求助的青年不失望而暗自难过”。 让亚洲学堂弟子倍受启发的还有面对面的改稿会。每堂课前,亚洲老师都会让学生带上自己的作品,他会一篇篇读,一篇篇评,谈优长不溢美,谈不足不避讳。亚洲学堂的十几名学子,闻道有先后,禀赋有高低,亚洲老师看中的只是对文字的那份虔诚。文学面前,人人平等。文学的进步和人生的进步,也许没有特别的对应关系,但又多少有些相关,把文做好了,把人做好了,很多事就水到渠成了。 50多年前,流离美国的张爱玲最后一次见到同样身在异乡的胡适。年少时书架上的名字就站在面前,偶像老了,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像,仍让这个天才奇女如对神明。 拿这个比喻略微引申一下:站在亚洲老师面前,也许你也会想到,一个文人所能有高度、厚度与宽度。 |
相关阅读: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8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7
·这位四川总督,是个清官! 2022-01-19
·泉州的一个民俗浓郁的小渔村! 2022-01-17
·【欣赏】黄亚洲:凡人故事(外三首) 202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