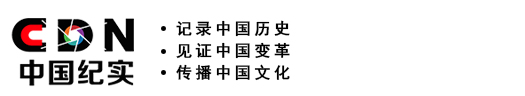黄亚洲专栏
黄亚洲随笔一组《笔写小平,心有大潮》
随笔一组
笔写小平,心有大潮 黄亚洲
1、艺术竟是如此相通
她是一位画家。这一刻,她正伸过她的思路与画笔,触碰我们正在打磨中的一个电视文学剧本。 也就是说,一位画家,开始评论文学。 她的发言,能使我感觉到一个美术工作者的色彩。她使用的水墨色彩,很是缤纷。 色彩之一,竟是音乐。 她是这样说的,我要强调音乐的重要性。一部长篇电视剧,一定要选好音乐。没有优秀音乐的电视剧,不会好看。 我很奇怪一个画家怎么会首先讲到音乐。这个问题不太有人说,更不会一开始就说。后来忽然想,赤橙黄绿青蓝紫,其实,是不是就是哆唻咪发嗦拉西?这么一想,便有点释然。 她开始评价节奏。她说这个本子,紧的地方多了,松的地方少了。有的地方完全可以抒情,可以浪漫。国外片子的那种追逐打斗,其实不是节奏紧张,是休息,是情节休息。文武之道,须一张一弛。 我理解,文学叙述中的张弛之道,或许就是一幅画作的疏密结构。画家是把我们的剧作看成了铺在她画案上的一张大尺寸宣纸。“情节休息”,这个词用得传神。 很意外,她甚至讲到了水的作用。她说,你们要把握好水! 这时候她就眯起眼睛,抬起短发下的圆脸庞,开始微笑。她说,剧中主人公,不是在1976年,在他遭批判的危难时刻,为防窃听而机智地在卫生间拧开自来水笼头吗?这不就有了流动的水吗?这不就慢慢地积了一盆很清冽的水吗?然后,应该,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个水潭,然后,水潭就翻卷成为一条河流,然后河流汇成大江,大江汹涌出海,这就出现了波澜壮阔的生机勃勃的大海。 大海的襟怀,多么的开阔与深沉! 她说,我呀,一直就是想到这水,水的流动。水,一定要运用好。 我想,一幅画,抑或是一部剧,真的都必须有灵动的东西。这是意韵,是任何一个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的闪动的眼波。 从涓涓细流到大海,当然,这不是在说水,是在说人,是在说一个人的人格。 说到这个人,她还直截了当说:其实我们不止一次说过,我们的父亲早就不是属于我们家的,是属于国家的。 我想,不管哪种样式的作品,艺术真的都是相通的。你看,一个画家,对一部剧作谈自己感觉的时候,能说到音乐,说到节奏,说到水和大海,多么的有意思。 这是一个艺术的下午,北京太阳很好。她侃侃而谈。她能启发我们,我们也能理解她话中的种种色彩。 我们捧着茶杯坐谈艺术的地方,是一个硕大的房间。这个房间是当年中国副统帅之妻的卧房与办公室。想想历史,历史疏疏密密,也挺艺术的。 画家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比我大八岁。数年前她携一百多幅画作在香港举办画展,作品被一抢而空,这个新闻我记忆犹新。她师从李苦禅,她对艺术确实是有深究的。 她姓邓,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大女儿。
2、小平数樱桃 坐在京城六月的风里,尤其是坐在这么一个近两亩的五彩缤纷的院子里,谈论一个伟人的种种事迹,且大都是与家庭生活相关联的一些事情,特是惬意。 青砖房子倒是一般的,两栋,都是二层,呈“L”形,偏是这个院子面积大,且缤纷,有树,有灌木,有草,延伸着爬上青砖墙的便是绿油油的爬山虎,爬的面积好大。 毛毛在我们没有坐下前,也是先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这个院子。她说老爷子早先就说过,房子不讲究,但是院子一定要大一点的。决定给老爷子修这个房子的时候,老爷子还在台上,因为原先住的房子小,所以要修个大一点的房子搬过去。谁知刚开始修,老爷子就又一次被打倒了。待到老爷子第三次上台,巧了,这房子也刚刚修好,像是候着他似的,所以就搬进来了。 院子里原来的树只有三棵,一棵是双龙树,其实是紧挨在一起的两棵松树,另一棵是更高大一些的白皮松,再一棵是百年石榴。现在我们看到的雪松以及其他树木与花草,都是后来自家陆陆续续补种的。总之,这个大院子现在已俨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了,散步其中应该是极为舒适。据说,小平就常散步于绿树之间,当那株百年樱桃红果累累之时,小平就曾驻步树下,仰脸数樱桃,一、二、三、四……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一百零四……毛毛无意中提及的这个细节令我很感兴趣,一是说明伟人也是常人,也有童心,可爱得很;二是又一次证明了小平对数字的敏感。我知道小平无论是作报告还是私下谈话,都是喜欢引用各种数字的。数字不仅是思想的体操,而且是思想是骨骼。每个务实的人都喜欢数字,数字体现精微。 小平喜欢桥牌,其实这也是一种高级的数字运算。我后来在他书房的玻璃书柜里,看到了并立摆放的三张奖状,都是桥牌协会颁发的,北京桥牌协会1995年颁给他的是一个称号:“远东杯名人桥牌赛最佳防守”;第二张是中国桥牌协会颁发的,更早,1986年,颁的是一个头衔:“兹聘请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而另一张则由世界桥牌协会颁发,颁的是一句话:“感谢他为世界桥牌发展及推广之杰出贡献。”看来小平很珍视桥牌领域的这些荣誉,把它们端端正正展览在自己的书柜里,这是一个人善于理性思维的证明和荣誉,不像有的领袖一样,建国之后只有感性思维,诗人气质,不停地大跃进,放卫星,最后是自说自话的“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弄得一败涂地。 说到这里,又想起早上出发时走的路径,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是从毛家湾一号集合出发的,这个院子曾为林宅,我们出发前又一次特意观看了副统帅的办公室,那办公室里有两台黑白电视机,一台小的是北京牌,一台大的是进口的;又在副统帅夫人的办公室里看见了一台特大的地球仪,这让我一下子联想起了当年号召“世界革命”的雄心壮志,我们那些年都饿得人瘦脸黑的,但红袖章上那团“解放全人类”的火焰却一直燃烧不熄。后来我们就驶离了毛家湾,越野车转了两个弯后驶入地安门内大街,不多远就是米粮库胡同,然后大家下车,络绎走进了曾有伟人数樱桃的那个花草斑斓的院子。 我们的行车路线活像中国的当代史,只转了几个弯,就是迥然不同的别一境界。 要感谢伟人的精于计算,他算出了穿蓝色补丁衣服的十亿中国男女的腰包里到底有多少铜子儿的答案,并且迎着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去改变这个答案,并且,谢天谢地,他也成功地改变了这个答案,让苦苦折腾的中国大地真正实现了“莺歌燕舞”,就像他每天散步的这个灿烂的院子。 其实,也不要说他只懂数字而不懂得浪漫。作为政治家,他也很懂浪漫,“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后代解决”都是想象力奇特的浪漫,鲜有政治家能提出如此新奇的思路。我在他的玻璃书柜间,还看到一件精致的圆形“玉龙”雕件,据毛毛介绍,这还是海峡对岸的一位极有知名度的人物特意托人带来的,由于受礼者属龙,所以这件礼物颇可解读,颇有深意,考虑到事关敏感,恕我这里对赠礼者的身份守口如瓶。当然,如果这种神交继续向纵深发展的话,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又将突然展现出一种令人陶醉的浪漫了。小平真是不乏浪漫的,也如他经历中的那种三起三落。 但是要指出的是,小平的所有浪漫思路都是建立在他的数字模型基础上的,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清晰地知道自家的粮仓里有几斗米,自己的箭匣里有几根箭,他不说过头话,他脚踏祖国的大地,他认认真真地数樱桃,他不做好高骛远的事。 他改变了中国。 而且是,方向上的改变。 当然,他若数到了几粒带血色的樱桃,并且有意未将它们计算在内,我们也不要过分苛求他的计数方法。每个人的方法都有一些问题。 小平谢世前有嘱咐,将自己的遗体提供医学解剖。据毛毛介绍,医生后来感叹说,他的心脏很健康,是四十岁的心脏;这时候毛毛的二姐插话说,她当时听说的是三十岁的心脏;这时候毛毛的大姐又更正说,医生当时说的确实是四十岁的心脏。我想,不管是三十岁还是四十岁,小平的充满朝气的思路和活力,仍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的状态写照,三十至四十之间,尚属年轻和稳健。 我的八十多岁的母亲,由于“帕金森”而多年站不起来,但她听说我的一部分写作涉及邓小平,便两眼有神,每一次见我辞别,便用微弱的声音说:快去,快去,不要管我,不要讲时间,也不要讲稿费,你快动身。我好几次从北京回来,她见我便问:啥时候电视放? 我说早呢,剧本还在一遍遍改呢,她的眼光每次都会暗淡。我知道,她是怕自己坚持不到看见荧屏邓小平的那一天。她曾是月薪24元的民办小学教师,由于邓小平一次又一次的复出而工资大幅飙升,也不再填写“家庭出身地主”那样的表格,最后以“五好教师”、“高级教师”的身份退休,甚至退休后还不停地加工资。所以一提到“邓小平”三字她就两眼有神,尽管声音微弱。 多少善良的中国百姓,心系小平。 小平数樱桃的时候,我相信,其中必有一颗,是我母亲。
3、看见青草与看见孩子
这位画家最先讲到的是看见青草,最后讲到的是看见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邓林大姐的腰不太好,她不能在高大的沙发上久坐,更不要说直挺挺地坐一小时,但在这个阳光和煦的冬日下午,她硬是在这张高高的沙发上坐了近一个半小时,她指着相邻的一张沙发说,老爷子每天坐的就是这一张。 他说的老爷子,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这次聊天的话题纯粹集中在邓小平的生活起居领域。因为出于下一步的写作需要,我迫切想了解细节,譬如饭量、睡眠、洗脚、散步、穿衣、香烟过滤嘴的长短以及哪一年由激烈的白酒转为柔软的黄酒等等问题,邓林大姐也爽快,说凡我知道的我都说吧。 这七零八碎地一问一答,就大大超过了一个钟头,双方都很有兴致,但我事先不了解她的腰痛问题,直到握手辞别,陪同的小王才说起他在一旁很紧张,因为他知道邓林大姐一直没有在高大的沙发上连续坐过一个钟头。 真是令我不好意思。 但是我离开米粮库胡同很远了,邓林大姐一开头说到的“看见青草”与最后提及的“看见孩子”,一直在我脑海里走着画面。画面不仅鲜明,而且鲜活。 “看见青草”,是说邓小平总是头一个看见庭院里的草色绿了。 草色的发绿是不容易看见的,近看更是看不见,常人看见的只是熬过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衰草,仍在寒风中微微打颤,常人只说:啊,这个冬天这么长呢。 但是邓小平说,哟,你看草都已经绿了。 他欣喜地指着左边、右边与前方,对身边的人说。有一年是对身边的女儿说的,有一年是对身边的警卫说的,这时候谁在他身边,他就指点谁看不容易看到的春天。 邓小平每天都在这面积有两亩大的庭院里散步,上午十点一次,绕十个大圈,下午三点一次,也绕十个大圈。他一边想着国际与国内,一边眼望着脚边与远处的青草。 青草最初的那种朦朦胧胧的绿色,肉眼是很难看出来的,只有在某种角度下,大片地望去,才能突然发现一种近乎鹅黄色的淡淡的浮云般的绿,而每一次,庭院里的这种最初的绿色,都是邓小平先发现的,这时候他就忽然站下来,很开心也很认真地对正好在他身边的一个人说:哟,你看草都已经绿了。 他在残冬看见春天了,或者说,他看见我们常人看不到的春天了。 我们经常唱《春天的故事》,唱“有一位老人在祖国的大海边画了一个圈”,其实,在“画圈”之前,这位老人的心里早已有最初的鹅黄般的绿色了。 青草的颜色就是蓝图的颜色。邓小平是超前的。 我感动于邓小平目光的犀利,而且,是在那样的吹拂不止的寒风之中。 “看见孩子”,则是指邓小平看着孙辈时眼睛里发出的光芒。邓林大姐十分诗意地说:他一看见孩子,眼睛里就有一种柔和的光。邓林大姐马上又解释:这句话是我说的,是一种形容。 我倒觉得,这不是形容,而是一种实在的叙述。一个戎马一生“三起三落”的老人,一看见孩子双眼就发出柔和的光,是特别容易理解的,也是特别真实的。 邓林大姐说,当上午十点过后,也就是当邓小平看完大叠的文件之后,她的母亲卓琳有时候就故意把几个孙辈都“集中”到邓小平办公室,任孩子们满地滚啊爬啊疯成一团,其中有个特别调皮的还会像孙猴子一样直接从窗户里蹦进来,卓琳就想以这种局面让丈夫得到片刻的“休息”,而且卓琳还事先准备了“道具”,这是特意为邓小平准备的,是一只粉色的塑料盒,里面放着糖果、饼干,以便让邓小平接下来拥有更为愉悦的动作:来来,爷爷给你吃块糖!来来,爷爷给你吃块饼干! 邓小平一边分着盒子里的糖果,一边还不忘幽默地感叹一声:我呀,就这么点权力。 邓小平的“这么一点权力”,多么的可贵。一个老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看见孩子会眼露“柔和的光”。说到底,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存在。上一代人的这种“柔和的光”,不仅使下一辈感到温暖,整个社会都会产生暖意。 而且,看见孩子随地滚爬,甚至看见有不合常规的动作,譬如像孙猴子那样从窗外跳入,也照样不减少“柔和的光”,照样把手伸进那只粉色的塑料盒中去摸索,照样取出慈祥和甜蜜,这就是一种境界了。 如果所有的掌权者对后辈都具备这种心态,多好。 总之,能首先看见草色泛绿的人与总是能用柔和眼光看待后辈的人,肯定是伟人,也肯定是平常人。 伟人与平常人,通常总是同一个人。 4、探班《邓小平》剧组
探班电视剧组,从来是件新鲜事儿,也从来是件劳苦事儿。说苦,是因为剧组人员的日常生活十分艰苦,哪怕偶尔去探班的人也会多多少少沾上苦味,回来就感叹,没想到这些大腕们、中腕们、小腕们一个个都那么惨烈,但是这一回探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组,却没想到这个剧组的弟兄们,更会苦到这种程度。 本来想,这部38集的电视剧拍摄,由于题材的重大与各方的关切,再加之资金的充分,并不至于艰苦卓绝,但是一进棚就觉得情况不妙,首先是这个三千平米的大棚里回荡着一股浓浓的甲醛味,因为临时搭建的房子体量很大,几乎整个儿邓家都“搬”在了里面,包括邓小平的办公室、大会客室、家庭餐厅、宽宽的走廊、气派的门厅,仿得惟妙惟肖,所以使人头昏脑涨的甲醛味儿就再也无可避免。其次是阴冷,大棚里面比棚外露天还要冷,外面天气虽是零度毕竟还有和煦的阳光,里面就只有打寒颤的份,尽管剧组的人一个个都裹着棉大衣。再者,是灰尘大,这可能与施工不久有关,建筑材料的粉尘总是在空中弥漫而不甘心沉沦。剧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包括那些大腕们,从早上开始就要在那里窩到深夜,一遍遍地听导演喝令“再来一遍”。怪不得我一进棚子就看到那么多人戴口罩,白的、红的、黑的,真不是开玩笑的事。 戴着厚帽子的把口罩推在脖子处的导演吴子牛,一见我就说“我感冒第五天了”,又说,我们这间屋子的全感冒了,人称“感冒屋”,又说,其实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大家的心理疲劳期已经过了,现在是生理疲劳期,免疫力特低,每个剧组都会先后来这两个疲劳期,尤其是我们这个组,毕竟连续拍了七十几天了。吴导说的这些经验之谈我都没有听说过,只是感到惊讶。 更惊讶的那些演员们,动不动就赶紧把棉大衣脱下来,只穿单衣,甚至是短袖单衣,在摄像机镜头前谈笑风生。原来今天拍的是“为邓小平过生日”,八十大寿,论季节,就是盛夏,八月二十二日,最热的日子,怪不得站在“邓小平”身后的“大女儿邓林”手里还拿着一把大蒲扇,不时地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穿短袖衣的“父亲”摇两摇。那演卓琳、邓朴方、邓楠、邓榕的,也一个个都是单衣,一边冻着,一边笑着。能不笑吗,父亲八十大寿呢。 我心里在想,这“一家子”都冻出鼻涕来怎么办?鼻涕可不是忍得住的,还有,咳嗽也不是忍得住的,寒颤也不是忍得住的,但这一家子就是在那里其乐融融,一会儿打趣,一会儿拍手,一会儿为电视机里的中美足球赛大声喝彩,还得忍受导演的残酷的“再来一遍”的吆喝,以及在“再来一遍”之前的化妆师的快速补妆,在脸上描描画画,在头发上拍拍掸掸,这一刻他们仍旧身处“盛夏”,手里拿着蒲扇,忍受摄影棚里出奇的寒冷与自己鼻孔里的液体。 特别佩服的是男主角马少骅,他不仅能老是穿着短袖白衬衫忍着严寒,没有一声抱怨,而且他的表演也比起一个月前我在开机座谈会上见到的那几个片花镜头,更见轻松。我说你现在特别放松啊,这位“邓大人”就用四川官话悄声回答我“我拍的戏里头,有很多很好的了”,看得出他的自信。尤可贵的是,他在表演中还有不少创造,譬如他得意地告诉我,在即将排演的“子女送生日礼物”的一场戏上,他已经想好了,从“女儿”毛毛手中接过一只新手表而换下那只戴了四十年的老表的时候,他应该说一句什么,因为剧本上没有提供相应的台词。接着,他就点着自己的手腕,用斩钉截铁的四川官话对我说:上紧发条,继续前进! 我说,好,得体!他笑,得意。 说起“二度创作”,吴导也有好多新的构想,譬如他说,在拍邓小平在301医院做前列腺手术的那场戏时,他就想到,以后这里一定要加拍一场邓小平的梦境戏,邓小平应该回到四川广安去,在老家看见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正面带愁容地计数着银洋与“串子钱”,算着十六岁的儿子邓希贤漂洋过海去法国要带多少学费,这时候,这位老年的邓小平应当悄步走近她的父母,默默地凝视着他的父母,双方可以没有任何台词交流。吴导说,因为邓小平自从离开老家,终生未回过故乡广安,所以在做手术之前应该有“见到爹娘”的这一场梦,这是人之常情。他说,我想好了,这场戏就到广安去拍,拍完了,就在那里举行关机仪式。 我听了这些都很感动。作为编剧之一,我很感谢这些添枝加叶的艺术创造, 我发现整个剧组的艺术投入程度都很高,正如另一位编剧张强所说,这个剧组是他所见过的风气最正的一个剧组。张强是经常来探班的,剧组在深圳拍戏的时候他也去了,干了许多超出编剧范畴的杂事,也算是半个剧组的人了。 大棚里的甲醛味、阴冷与扬尘使我打了好几个喷嚏,于是赶快跑到大棚外换空气。北京的空气本来已不怎么样了,大棚里的空气更是雪上加霜,这拍戏真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何况日日夜夜连轴转,想到这里,不能不对演员们平添一份敬意,再也不羡慕他们手捧鲜花接受粉丝欢呼的风光了。 制片主任一直站在棚子门口,看着他的各路手下人的忙碌,也看着送饭的车子把一份份简单的盒子饭递到大家手里,于是众人接过饭盒都蹲下来,就着阳光和冬风哗哗地扒饭。这位处事严格的高主任告诉我,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安全地带好这四百多号人,稳住这支队伍,要“维稳”就要讲和谐,所以“邓榕”前几天过生日他特地备了蛋糕,叫“邓榕”好一阵感动;即使一般的工人过生日,只要他了解到,最起码也得关照一碗热乎乎的“长寿面”。他说,你想,四百多号人,几乎天天都有人生日呢,这些小事都是不能小看的。他又哈哈笑着说,组里那帮人以前都叫我“政委”,现在改叫“书记”了。这位浓眉大眼的高主任曾经领军过《建党伟业》与《辛亥革命》的电影摄制组,一脸的威信与一肚皮的经验。 眼前的这个三千平米摄影棚与相邻的那个两千平米摄影棚,同属一个叫“八仙文化产业园”的单位,位于北京北面的五环与六环之间,据说很兴旺,已经拍过《天下无贼》等许多影视作品。我身旁的起重机则一直叽叽嘎嘎地叫着,一排高高耸立的钢柱子预示着第三个摄影大棚即将诞生。首都的影视产业方兴未艾,作为一个舞文弄墨写剧本的,看到这种情况固然高兴,然而想到严严实实的三千平米棚子里的甲醛与灰尘,还有那彻骨的阴冷,心里便寒,这种苦可不是常人都能吃的,何况还要穿短袖过“盛夏”呢,何况还要摇扇呢,何况还是连续几十个日日夜夜呢。 为了“欢送”前来探班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以及我们这些人,马少骅专门换上了一身灰色中山装,跑出摄影棚,向发动的汽车频频招手,显示“小平同志”对众人的关怀。在招手告别前,他还一一与人照相,单独也照,率“妻女”也照,尽显和善慈祥。他最后的话是“你们放心,我们一心一意拍好”,也是标准的四川官话,一字一顿,像煞邓大人口吻。 在“小平同志”这样的话前面,我们这些探班的人,除了感动,还能有别的什么呢?
5、戴着口罩写文章
出地铁口,再戴回口罩,步行十分钟,到小区,上二楼,按响电铃。 一进门我就习惯地大声说外公最喜欢花花了,花花马上就说我最不喜欢外公了。我说鞋呢?花花就打开鞋柜,为我找出一双拖鞋,表情认真得像大人。我一穿,只能塞进脚掌,半个脚后跟踩在外面。因为不忍违拂了花花的好意,所以紧紧地顶一顶脚,也就穿上了。 这时候安东就从他的小房间里大步出来了,手里拿着平板电脑,说外公你看,这款游戏的画面角落有枪,可以是冲锋枪,也可以是手枪,可以射击,但是画面背景出现的是实况。我一看,果然,画面里晃动的正是我们房间客厅的实况。我于是立即走到他的镜头前面去,听他按动按钮,传出装弹以及弹夹上膛的声音,然后就是开火的达达声,我于是痛苦万分地捂住胸口,倒在沙发上,不仅倒下还要再三挣扎,我知道影剧里的主人公都是死得很艰难的。 花花的大名是王雨禾,她哥安东的大名是王柬禾。 很迟开饭。因为女儿一般都是拖延着下班回家,进门就疲惫万分的样子,有时候嗓音还是嘶哑的。我给她看花花给我找的露出半个脚后跟的拖鞋,女儿就笑,说花花从小就会给外公穿小鞋了。这时候安东就让母亲看电脑里的回放,女儿看着就评价说,还是外公死得最像,我们都死过好几回了,都没有外公死得像。 女儿对于演技的评价应该是有权威性的,她近年制作了好几部热播剧,像《辣妈正传》、《大丈夫》、《团圆饭》什么的,观演员无数,看来我在她的心目中只能发生“演员”的联想,而不发生“编剧”的联想。她对我热衷编剧“伟人戏”一向兴趣缺缺。 然后是吃完饭,然后是继续与花花和安东玩一阵,然后就是出门钻地铁回我的小酒店。走去地铁站的路上,也照例严格地戴起口罩。我来北京买的口罩已经有好几打了。 除了回女儿家吃晚饭,整个白天都在一家颇有实力的出版公司“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写作。写作的样式是“口述”,有一位北大研究生学历的派来作为打字助手。这出版机构真好,肯这么地花大本钱。因为写的是长篇文学作品《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算是选题重点,又要赶某个进度,所以出版公司也就超常规操作了,他们知道我的打字速度实在阿弥陀佛。 自去年十一月始,到如今杨花如雪的暮春,整半年里,我除了节假日几次返杭,基本上都在北京过“上班族”生活,办了退休还这么紧张,以前哪里想得到。幸亏初稿的写作已临近尾声,剩最后几万字了。 在北京过日子能每天享受天伦之乐,当然是好,也可以解解整日“口述”的呆板之烦。但是叫人皱眉头的事情还是有两桩,我一提起就愁。一是干燥,尤其是冬天,皮肤都裂得痛;二是雾霾,过去只知道叫雾,后来知道是霾,在骆家辉当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才知道叫PM2.5,这才痛感到鼻子与咽喉怎么会这么不舒服,这才学着北京的路人赶快戴起口罩上下班。 我们总有人要厌烦骆家辉,指责他“说三道四”,在大使馆围墙上竖起空气测试仪是“狗咬耗子”。但是我想,要是美国佬上回不是派的骆家辉履职北京,而是派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不说三道四的,那我肯定也是省了买口罩钱了,也不会知道PM2.5将会如何更密集地亲近我的肺叶和气管了,也不会知道我的伟大首都其实根本不是一首美丽的朦胧诗了。 说到底,狗能咬住耗子也是好事啊。按照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逻辑,也该给以表彰啊。我们这时候确乎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要把人家提醒我们的善意一律当做“亡我之心不死”。 这半年来北京的蓝天次数实在不多,真盼望北京多刮风能刮出白天的云朵和晚上的星星来,可就是老不刮风,蒙古高原上的风怎么这么偷懒啊,越来越不像成吉思汗了。 每天十几次把口罩戴上取下的日子确实过得窝心,更叫人窝心的是一位陌生朋友好心地指出我买的医用口罩太薄,根本挡不住那个2.5,说你戴口罩与买安慰剂无异。那一刻心里真窝火,真有点想骂一声“狗咬耗子”,就如我们骂骆家辉一样。 难道真的要叫一街人都戴防毒面具吗?一个崛起大国的首都天天都该是防化演习的状态吗?不过,我后来倒是连着跑了好几家有口罩卖的店家,但都没有那种猪八戒式的严严实实的。大约买的人多,脱货了。 我还是戴着我的薄口罩每天去出版公司“口述”我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傍晚戴起薄口罩急匆匆连赶两路地铁去女儿家,在家里的沙发上再完成一遍我的“死亡”过程。过着这样的日子,就不由得更深沉地思索起邓小平他老人家来了。我躺在床上想,他老人家知道改革开放几十年后有如此严重的环境之虞吗?知道那些贪官外逃明明是为藏金掖银却推说是“国内空气不好”吗?知道狠抓“发展是硬道理”但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步推进会有如此令人不安的后果吗? 但是想想他老人家也难,把一个国家从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泥潭里拖出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背脊上已经被人指指戳戳说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了,再要他把人类进步的所有道理都整理明白,都做得左右兼顾严丝合缝,也是难为了。 他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心里想的也是怎么尽快让中国老百姓富起来,也算是找着相对真理了,算是高屋建瓴了。想到这里,我尽管每天戴着口罩走向出版公司大楼,心里也是平衡的,也是想着如何兢兢业业塑造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光辉形象的,伟人不是全能者。 当然,我这里想的,不能写在长篇中。这个分寸,我还是掌握的。 关键是,眼下的社会,可不能再过分强调“摸石头”了。要想着“桥”的概念与“船”的概念了。许多事情既然已经看清楚,手里就该有一张全新的路线图了。 总设计师当年来不及描清晰的笔划,现在该有人来接笔了。 不然,像我这把年纪的,弄得不好,真就要早早地倒在沙发上了。 那时候的挣扎,可不是演戏。
6、审片《邓小平》五昼夜 我这人泪点低,这几天又一次得到了确证。看“非诚勿扰”与“中国梦想秀”都经常是有液体夺眶而出,何况审看的是52集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部泪点这么多的电视剧。 连着五天,经受着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深深浸染过的一段历史风云。 风云很重,迎面拂过面颊的时候,水汽就凝结了。 不仅仅是邓小平经受的风云,是我们大家都经受过的风云。当然,邓小平经受的烈度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多,他的大儿子至今还是高位截瘫,“文革”逼的。 果不其然,坐在第一排沙发上的邓家三女儿,从一开始起,就掏手帕或者纸巾抹开了眼睛。这第一天上午的审片,只安排放三集,请邓林、邓楠、邓蓉都来离首都机场不远的一个僻静地儿一齐观看,然后,就不再请她们集中了,让她们携上带子回家看,剩我们这些主创人员与联合摄制单位的头头们封闭式地连看五天,每天都得十集以上。 家属的意见自然特别重要,要是她们说此剧的主人公没有她们家“老爷子”的那股精气神儿,那我们就惨,这几年算是白写,剧组这半年的劳苦也是白搭。 吴导演与制片主任倒是信心满满,说估计问题不大。果然,头天上午的放映一结束,灯光亮起,就见邓家来的三位大姐都眼睛红红的。邓榕情绪最激动,站起来就大声说:有人告诉我,你开始看可能还觉得不像是自己的父亲,看到七八集之后就能接受。我今天看到第一集就接受了,这就是我家老爷子! 邓榕讲的是实情。我是只几个镜头一看便认定这是邓小平了;更早一些,半年前在北京摄影棚里探班的时候,就觉得那个马少骅的一举手一投足就活活是邓大人不假了。 马少骅在影视剧里演过六次孙中山,演技精良得很,这回扮邓大人,据说可以用“风魔”来形容了,每夜干完活儿还不睡觉,还在自己房里看回放,一遍又一遍,琢磨着举手投足与台词。半夜过走廊的,只要走过他房门前,都能隐约听见邓小平的“川普话”。 已经有人评价这位马少骅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了,断言今年八月由央视播出这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后,他必身价翻倍,以后中国的老年邓小平角儿非他莫属。 看“老爷子”在画面里吃力地为半瘫的儿子擦身、在准备“被逮捕”前吩咐将家庭照片分送各位子女作纪念、在急病送院时分的冷汗淋漓、复出后在“两个凡是”的重压下夜不成寐、在听说云南知青为回城“罢工”的时候痛下决心说“让孩子们回来吧”、在刘少奇还没有平反之时就公开把王光美叫上主席台与她当众握手,几乎所有的审片者都看得鼻孔发酸,一张张纸巾在一张张脸颊上走了又走。 一部所谓的“主旋律”电视剧,能看得人不停地抽鼻子,也算够意思了。 不过,也许,特别容易感动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感觉到的泪点在年轻的孩子们看来或许是笑点也说不定。这么一想,就是个问题了,还真不好说。 中午围桌吃饭的时候,邓林在邓榕的催促下,也发表了一段观感。她说,这戏拍得不错,首先是编得好,每集都有一个中心,比如“逃港”那一节,就吸引人。另外,演员不错。老爷子那些重要的话,马少骅能用很平实的口吻说出来,特别的好。 后来,邓榕也说了一些内行话,她说这戏已经这么拍了,也没法改了,比如北京301医院的女军医头上戴的无檐军帽,不是这么个戴法,不能压着额头的,帽子要往后推。当然我知道戏没法再改,现在也不过是这么一说。 这么的通达,其实是表达了对这部戏的真正的喜爱。 随后的几天里,在家中的邓榕也不停地给这里发短信,说她现在看到第几集了,又流了几次眼泪,等等,直说得我们这些在这里昼夜审片的越来越心里瓷实。 连着看了五昼夜,颈椎与腰椎都有些生锈。人有了木偶的感觉。但是脑袋里,活泼得很,哗哗哗有流水声。 历史其实就是活泼的,是大家的,不是考古学家专用的。 太应该回顾这一段历史了。 审完52集,大家围坐一起讨论之时,邓家的三位女儿再一次赶了过来,邓楠进门就连声说,这两天每夜看到早上四点钟啊。邓榕一见吴子牛就寒暄:导演劳苦功高! 在座谈中,邓榕说她在家里看的时候,一摞纸巾就放在旁边,几乎看每一集都掉眼泪。她说,我丈夫平时看影视剧是最挑剔的,这回是说了八个字:相当精彩,相当成功。 邓榕又说,很喜欢扮演剧中人 邓楠谈到了剧中人的说话口音问题,说原先一直是主张影视剧中的“老爷子”说普通话的,这次一看,四川话是帮助“老爷子”树立了形象。邓林的感叹也很有趣,她说原先还是用“审查”的眼光来看的,但看了几集就看进去了,就像普通观众一样的看。她也提了一些改正之处,觉得刚性的东西还是多了,要有一些柔性的东西,毕竟是艺术作品。 画家还是看重艺术。 现在我担心的,还是收视率。我们这些人当然是看得热泪盈眶,这家家户户呢,尤其是年轻人呢?不要又落得添一个“主旋律作品没有收视率”的实例。 这时候,只听来自央视的那位负责同志斩钉截铁断言,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家重大革命人物电视剧拍得最好的一部。他也嗓音很响地估计,收视率没有问题。 这就放心了。虽说,还只是预测。 认同的,不是一部电视剧,不是编剧与导演,不是马少骅,是一段历史。 再往政治上说,是一条道路。
附记:此随笔发出后,饰演邓小平的马少骅老师即发来一则手机短信:“亚洲老师好!今天我看了您审片后的意见和对我的鼓励,谢谢!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努力奋斗能让大家接受和喜欢,更希望小平家人的肯定、专家认可、上级领导通过。这我就放心了。这些成功都与您们多少年的苦心努力紧密相连,!辛苦了亚洲老师,谢谢您!”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的谦虚与拳拳之心跃然于文字,令人感动。在我感觉中,他已得小平之精髓了。
7、笔写小平,心有大潮
参与六十万字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写作,我一直是怀有个人感情的。要不是笔下这位超凡脱俗的主人公对于中国的勉力推动,我的父亲可能一辈子不会接到他梦寐以求的那份“平反错误”的红头文件,我的母亲还会继续在她的教师生涯里上百遍地填写“家庭成份地主”的屈辱表格,我的后半生也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也有可能还在每天用粮票丈量自己的肠胃,以布票比划补丁的尺寸。 小平同志对当代中国的推动委实太大了。写作是一种怀旧,在这部作品的一些虚构人物的身影中,确实有我个人清晰的影子,比如乡下的“知青”,比如重圆大学梦的学子。 再过几天就是邓小平诞辰是110周年了,我愿意再写一首小诗纪念他:
写你的名字,笔划特少,少得像真理一样单纯;喊你的名字,调门特顺,顺得像百姓人家最爱取的小名。 大声说出你的名字,是在那一年寒冷的开春。我看见,父母脸上,干涸的河床忽然湿润。我不是在说,我自家的父母从此恢复了名誉;我是在说,一个民族,瞬间,获得了自尊。 错字连篇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由于一句“实事求是”,终于有机会,全面校正。 春天的热身赛才刚刚开始,我们听说你又去了深圳。总之,这是一个有关速度的故事;感谢失眠的设计师,下笔有神,入木三分。 今夜,我又从梦中惊醒。月光里,有泪湿枕。该是一百一十年的诞辰吧?我知道,这不仅是关于一个人,夸张一点说,是关于一个时代,或者是,关于一个民族的诞辰。 那么,你现在好吗,小平?那炷烟头,还能一明一灭吗?想到你,总是听见中国铁路的声音:一明一灭之间,啪答叉开;又啪答一声,重新接准。 你现在好吗,小平?我们眼下的生活,已经,很有些滋润。我们每一次这么说的时候,脸上,总会有一些泪痕。 一百一十年了,我们想放一束玫瑰,但是很难找到那片云层。风,有时候很大,吹得泪水,也失去了瀑布之声。我想,记挂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或许,还是十几亿百姓,一日三餐,舒心干活,好好做人。
当然,感情写作包括理性写作,只是写东西的动力,真正要写好这种“大数据”作品,难度还是不小的。说到难度,一是写作分寸的问题,二是写作技能的问题。关于分寸,有自我设置的,有他人帮你设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故事年份靠现在太近,许多人健在,许多事众说纷纭,许多判断相距甚远,要在当下的环境里说好这些事情,没有分寸感是不行的,这种感觉比简单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方针还要紧。 关于写作技能,自己忖量,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从现在看,确是这样,尤其是长篇文学作品,内中描述的真切以及深入的程度,都还欠缺多多。有些是不敢写,有些是写不好。曾有好几个晚上睡不踏实,躺在京城小旅馆的床上,努力把自己变成领袖人物,努力设想自己有很大的情怀,有时候忽然也感觉到一点什么,半夜会跳起来,但是次日落实在键盘上,精气神又都跑了个八九不离十。说实话,许多时候,还是自己卡住自己,不是人家卡你。 好在笔下的主人公有高度,尽管要将他当作中国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写,尽管不是写神,尽管下笔力求平视,但小平那种内心的高度是客观的,他思考国家未来道路的那种格调是高屋建瓴的,他的意志力是坚毅的与一往无前的,所以他一旦活动在文字上,就有这么大的气度;他一出场,空气就活了;以至好几回让我在写作的时候热泪盈眶,内心有澎湃之音。 还是我上面这首小诗所描绘的,“你现在好吗,小平?那炷烟头,还能一明一灭吗?想到你,总是听见中国铁路的声音:一明一灭之间,啪答叉开;又啪答一声,重新接准。”在政治积习与文化积习都那么深重的中国,要力排众议,果决换轨,这个扳道工该有多么强大的意志与手劲! 就由于这个原因,使我们这部作品有了先天的气势与力量。打某种角度说,我们不是在写作,是跟在总设计师身后,描画一个国家的蓝图! 写作小平,心有大潮,那是必然的。 毕竟,这是一个时代的概括描述,而且这个时代离我们这么近,甚至至今一伸手就能摸到,甚至这个时代还扯着我们一起奔跑,还会不断奉献出新的令人振奋的历史转折,我想,这也是这部作品的一种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
相关阅读: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8
·黄亚洲|北京冬奥诗情(四首) 2022-02-07
·这位四川总督,是个清官! 2022-01-19
·泉州的一个民俗浓郁的小渔村! 2022-01-17
·【欣赏】黄亚洲:凡人故事(外三首) 202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