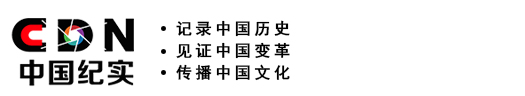人物
“人文光芒 艺术绽放”著名当代工笔画艺术家何家英专访
4月1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人民形象,中国精神”著名艺术家系列展第八场——何家英精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共展出了何家英先生30多年各个时期创作的40余幅作品,其中工笔画代表作20幅,写意画代表作20余幅,代表作有《山地》《十九秋》《米脂的婆姨》《酸葡萄》《魂系马嵬》《秋冥》《朝•露•桑》《舞之憩》等。 何家英先生是中国美协副主席,在工笔画领域有着很高的造诣,他为中国工笔人物画向当代性的转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读他的画,会从中找到一种真诚细腻的激情和梦幻般的理想色彩。究竟何家英先生的作品表达了怎么样的人民形象,又传承了哪些中国精神?对此,我们现场对他进行了独家采访。 记者:这次画展的主题是“人民形象•中国精神”,您的作品是如何表达这个主题的?您的作品如何表达个人的审美与艺术视角? 何家英:文化是人的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载体,绘画是特别直观的一种载体,从审美的角度宣扬着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影响着整个国家的价值观取向,每幅画都有着不同的内涵。中国是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国,特别是中国的绘画,是一种博大精深的艺术形式,有着非常灿烂辉煌的历史,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工笔画,工笔画的鼎盛时期,是在晋、唐、宋时期,那时候,工笔画是中国的主流绘画形式,也是中国人物画取得最高成就的艺术。后来,随着文人画的兴起,工笔画、人物画开始逐渐消减和萎缩,并转向于文人画的山水、花鸟画,文人画逐渐成为了主流。到了明清,工笔画也慢慢丧失了唐宋以前的文化气度和大国精神。 在我看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一句口号,是要复兴我们过去伟大灿烂的历史,复兴过去晋唐时期的中国精神,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深奥的、一种足可以使世界臣服的一种艺术的高度和价值观的主张。当今世界,有点趋向大同,但是这个大同是以西方的标准产生的一种价值观的整合,而中国,具有独立的文艺思想,有着悠久的灿烂的文化历史,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独到的主张,不追随别人的潮流。 当然我们不是封闭的,而是将中西方优秀的文化品质,融于当代的艺术创作之中,因为中国精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开放的精神,包容的精神。我们敢于跟你交流,敢于学习你的好文化,来促进我们自己的发展。既不忽略我们自己的传统,又要深挖传统的精华,而不是一般的挂在口头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它不仅仅是明清时期的文人画的传统,而是我们最辉煌的晋唐时期的绘画艺术,那种民族的气度和精神,是我们必须要继承下来的。任何西方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从中相融合,变成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有本体和主体,我们再开放,最后都要回归到中国文化本体上来,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中,我们要有所建树、有所发展、有所创造,从而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从文化角度讲,具体到工笔画角度讲,这就是扎扎实实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喊口号,那么对于中西相融合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结合,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它需要更加辩证地看待艺术。因为大家都知道,中西方艺术语言,是完全不同的、相对立的和绘画体系和文化观念。在这样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面前,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融合的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面前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往往被假象所迷惑。所谓体系的对立,常常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象的区别,而没有看到本质上的相似,就是共同的本质。 我们谈绘画的本质,它是由感觉、节奏、空间、灵性这样基本的语言来构成的,包括语言的笔触、线条、色彩等等。例如19世纪时期,清代郎世宁的介入,他采用古典主义的明暗法,揉到了中国画的材料表现当中,画肖像可以画得惟妙惟肖,就是说西方古典艺术是描摹自然的一种绘画,它是对自然的真实的再现表达,而中国画一直是抓住艺术的本质,它是对自然的感受、发现和描写,更重要的是更注重自己的主观意识,它是通过你的“心源”(这是个复杂的内心问题,包括审美、意识、哲学、观念、人文修养等等)把你看到的自然,再重新变为艺术,所以一部分画的也很写实,一部分又不是完全的写实。对写实的认识和表达中西方也不同,但是如果把西方的明暗的问题给滤去,只看它的结构和造型,你又会发现其实也非常的接近,要表达的根本的东西是一致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绘画是韵律的、有规律的程式语言,是对真实的结构关系的一种整合性表达。而西画则是讲究科学的、以表象真实为依据的模拟性的绘画。如果滤去了明暗等表象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的人物画在去刻画一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还刻画不到如此的真切、真实和精美,特别是人的个性与内心世界的表达。这种形象的表达是人物画非常重要的语言,但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中国画虽然也有形象表达,但是都属于类型化的个性形象,比如文人、罗汉、武士、大哭、大笑等等,都是一种类型化的,但是不管怎样,总体来说中国人物画含有一定的概念性,跟西方一对比还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所以我们要通过西方式的写生和对人物的深入挖掘。我们抛开明暗,就它本身的结构,审美的体验,完全是可以用中国画的语言表达的。在这里相融合的时候,我就把西方的优点融入到中国的绘画本体语言上来,而中国本体语言与西画有些表达上又特别接近,尤其是西方早期中世纪以前的绘画,也是程式语言的,是程式语言与程式语言不同,而程式语言不同又促进了我们对程式语言再创造的一种激发、一种参照。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了敦煌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别忘了,敦煌大部分是外国人画的,而不是中国人,它是中亚、西亚这些画师画的,整个敦煌有着相同的文化意识,一种绘画的理念,但是又有很多的不同,而不同之处之间又各有各的优势,各自的优势交流交融就促进了自身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汉唐的对外开放,疆土领域的扩张,使得文化经济之间的交融,我们又怎么会到了唐代产生如此的一种辉煌?唐代绘画格调之雍容、气派,每点都体现了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一种大世界的精神,是容的下别人的,是能互相交融的。所以文化也需要交融、需要交流。 今天就是一个交流的国际化的时代,我们与西方文化对话当中,要借鉴学习西方好的品质,好的长处,而避免那些邪恶的、丑恶的、腐朽的不人性的东西泛滥。现在的艺术提倡人的真实,所谓真实不是一个表象真实,是真实的思想的表达,不仅仅是表象理性下认识的所谓的自然和自我表达,同时也在极力提倡人在非理性情况下的自我。非理性里头,就包含了善与恶两个方面,尤其是在非理性时候,恶的东西,就是不符合道德观念的东西,就会被揭示出来。开始时艺术家可能会把它当做对丑恶的批判和揭示,但同时艺术家又是对丑恶的一种欣赏。因此审美同时存在着审丑,丑与美这个界限是一个永远讨论不完的话题。那么,现在提倡的这种精神真实,实际上就等于一下子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把魔鬼给放出来了,造成了世界性的一种丑恶的泛滥,我们才出现了很多不人道的惨不忍睹的一些文化现象。 中国有着自己的普世价值观,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画家,我们有责任提倡这种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中国的文艺理念思想,其实正是一种正能量的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所谓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其实就是提倡人类善良的人民共同的普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仍然符合世界80%以上的知识阶层的共同认知的,因为人的善良对美好的追求,道德对人的约束,对善的向往,是永恒的主题,也是永恒的追求,文化并不是简单的花花鸟鸟,它是对社会形态的一种表达,所以说文化是什么形态,社会就是什么形态。因此我们有责任提倡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当然艺术上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之分,现在的艺术是多元的、丰富的、自由的。但是我对自由两个字是有一定的看法的,人不可以无原则的自由,自由放纵自由就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自由一定是在人类的理智约束下的一种人性的自由。人性的自由是有利他性的,当你作为艺术家没有了利他性的原则,这世界是可怕的。我们强调了自我,就变成了非常严重的自私自利的自我,是一种小我而缺少民族情怀的、缺少人类关怀的一种大自我。艺术家不能仅仅停留在小自我上,还要有一种大的胸怀,对民族也好、对国家也好,对世界、对人民都要有一种关爱,要热爱人民。正是因为这样的价值观我们才要表现出来,讴歌人民,为人民造像,塑造人民的形象,因为在人民的生活当中,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当然生活不是艺术的唯一源泉,因为艺术的源泉还有其他的文化的源泉、艺术本身的源泉对你的滋养、刺激,但是,生活必然是艺术的源泉。没有了生活,没有了真情实感,你的艺术就是空洞的。像西方有些大师,不过就是在画室里头画模特,自己创造了一个形式而已,那跟过去的19世纪以前的那些伟大的画家,那样的一种气派,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我的作品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一种超越,所谓超越,如果放在历史长河当中看,我超越了政治的符号,超越了故事性,赋予了更深的人性,无论是我画《十九秋》《山地》《杨开慧》,里面都充满了对人性的讴歌,对人的命运的主题的表达,所以我的画很难定下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我们不能用这种概念来判定,因为我的作品里面还具有诗性的,我追求的是诗的意境,是中国文化特别本质的东西,中国文化非常强调诗的意境和境界。中国绘画并不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场面(除了宗教绘画之外),即便像《南巡图》也好,这样宏大的场面,都是像风俗画一样的东西,仍然不是一种现实主义主流的一种方式,但是,中国绘画特别会表现诗意,表现意境,是有境界的,增加了很多个人心性的表达,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就是自我内心体验的一种外化。我画的都是美女,实际上我画的却是我自己,我画美女的时候是用我的理解、我的心性来认识美女,所以我可以从女性身上发现美,对美的发现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能不能发现是人自身有没有这份理念的问题,庆幸我有这样的感受。 一个文艺工作者,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自由的,那我宁可选择这样的道路,在我人生当中,我只想做“正确的事情”,从小就是这样,不是因为有政治约束着我,也不是因为我在体制内如何如何?这是自觉的行为。八十年代的时候,是中国艺术重新觉悟的时代,我说的觉悟因人而异,但从整体的大潮来讲,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一个完全在政治体制下的一个标准的过程,那么中国画在新中国,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有着翻天覆地的进步,因为我们提倡的一点,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指导下,我认为是对的,所以,艺术家强调生活感受,跟民国清末是有天壤之别的,那是新中国所产生的巨大的艺术动力,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历史我们不能歪曲,但是这却是一花独放,并不是百花盛开,春色满园的。但在一花独放的情况下,有好坏之分,也确实产生了许许多多伟大的作品,也产生了几位大师,在新中国所形成的大师也有,很了不起!经过文化大革命,政治的因素越来越重,美术成为了政治的口号,政治的符号,产生了假大空的艺术样式,所以,那时候所说的工农兵,是一种符号的概念性的,人的拳头画的跟脸一样大,全都是笑嘻嘻的,完全是假的东西,工笔画更是和年画分不开,和宣传画分不开,和水粉画分不开,丢失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东西,也丧失了西方曾经在现实主义中或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所以,必然会让画家们产生一种抵触和厌恶的情绪,因此,国门一打开,世界的艺术一进来,发现艺术完全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样子,而是非常丰富的,因此,主要的绘画方向在探索艺术的本质的时候,是追求西方现代的艺术的,是这样一种潮流才产生了八五思潮等一些世界性的流行追求。在这样一种大潮的背景下,我们年轻人,该怎么走?是经过了冷静的、深思熟虑的思考,读书、看画册展览、横向、纵向来观察。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纵观世界美术、中国美术历史,一方面对传统的再认识,一方面对西方(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还是现实主义)都有一定的认识。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思考,我选择了这样一个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一种诗性的语言,尽管我不会写诗,但是我内心里有诗心,有意境。虽然手法上更加的写实,但却融入了更多的精神性的因素。我认为中国艺术、中国的绘画,在写实的方向上也是从过去的装饰意向到写实的过程,但是在写实这一块上没走完,走的调子也不够高。 记者:有很多评论家说您的作品在具象之外还有很多深邃的内涵,我们也在不断的解读您的作品,您是怎样看的呢? 何家英:在参照西方、参照古代晋、唐、宋的绘画时,你会对艺术会有新的认识。我意识到了艺术本来是个什么样子?好东西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有一个原则,用一个特别朴素的话说,就是好东西不能丢。就是我融于我内心融于我一身的是我全挑着最精华的经典的东西,不在于追求我的一招一式的小的个性。我也许会创造一个样式,很有特点、风格,但是这种风格的确立,可能也就流行五年、十年,被人模仿完之后就不存在了,就是你终就会被别人来取代。我要追求的这种高度,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也不仅仅是写实上的,更重要的是审美和精神上的,人和人的内心不一样,表现力不一样,认识不一样,是不能替代和不能重复的个性的人,所以我觉得,我选择的道路才是一种真个性,是我真实性情的表达。我觉得我从小注定了走这样一条道路,所以我认为也是一种个性。今天大家吹捧我的也是一看就知道是何家英的画,其实我的画没有特别大的特点,一点风格倾向都没有,甚至连签名都没有,大家还是知道是何家英的画,为什么?就是里面那骨子韵味,不是傻乎乎的画了个物体,是一个有精神的东西,画就是应该蒙上一种神秘的东西在那,无论是有题材没题材,有背景没背景,都需要有这种东西。 创新本身也是对传统的再发现,是一种创新的途径,一方面我发现了唐宋大传统当中的很多的重要的东西,一方面我们又发现西方的这些好的绘画精神和手法,很自然的融合到中国书画里面,你的方向是明确的,所以这30年来我并不摇摆,一直坚持这样的创作,逐渐的被人认可,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流行过去了之后才是扎实的完全得到大家的认可,才得到当代艺术领域的公认,一个人要有敢于坚持的精神,艺术是没有严格的标准的,走哪一条路都会有你的受众群体。我选择的是比较正统的一条大道,把精华的东西融入进来的一种方式。但是毕竟受到一些外因影响,比如说逐渐的出名了社会活动就多了,市场的繁荣也会占据你不少的时间,也会影响你的一些主题创作上的表达和表现,所以说后来真正的去创作一些作品就稀少了,特别是工笔画没有再画。但这些年来我没有停止对工笔画的学习和认识,我会重新来认识看待工笔画的。 我调到艺术研究院以后得到了院领导、部领导的鼎力支持,单独建立工笔画研究院,在中国工笔画繁荣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对繁荣的成就的归纳、总结、推出,另一方面也要解决工笔画行业在各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我也可能耽误很多的时间,但是更重要的,会让我通过工笔画研究院重新认识工笔画,激发我的艺术灵感,虽然这些年没有画,我相信我再画工笔画的话会有一些大的变化,不会完完全全的走老路,但是前提一定会有艺术感受和生活感受的。首先艺术感受呢,内心里积累这么多年应该有点意思,另外我会做一些考察,特别是对壁画的考察,它对艺术创新会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需要有真切的生活感受,如果没有特别感人的感受,工笔画画一张花那么多时间,如果只是追求一个外表的细腻好看,真是有点浪费生命,也没有意思。还是把心用在深入二个字上,深入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是真正的深入到灵魂中,深入到人们的真切的情感当中,来创造新的艺术,取得新的进展。 这次由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名家系列精品展,正好借此机会把我的系列精品进行了梳理和展示,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我的个展什么时候能搞?我很惭愧没有一些新的作品出来。我特别不敢在北京搞展览,因为北京是一个特别难搞展览的地方,这里的标准特别高,而且我这些工笔画也没什么新鲜的,大家都见过,不好意思匆匆忙忙的办展览。这次借研究院的系列展拿出来作为靶子,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更多的是可以在艺术上去交流,促进我自己的发展和在艺术上的进步。 记者:您刚刚多次提到中外文化的融合以及大世界的精神,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输出的? 何家英:我们文化的输出问题还停留在口号上,文化是价值观的体现,文化的交流,文化的输出,文化的世界性的宣传,是我们中国战略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我们还没有掌握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和渠道,我们还停留在中国式的一窝蜂式的展览方式上,简陋的展览没有学术主题的支持,没有雄厚的资金,没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所以想在外面产生影响的不可能的。挺好的画,没有好的方式和运作,也得不到人家的尊重。国外有很多文化中心,大使馆管理的文化中心,好多展览层次不高。起不到该起到的作用,你不能推出最优秀的中国文化,谈什么话语权?谁拿你的展览当回事? 文化输出问题,简单的讲靠三点: 1.确实有好作品,确确实实能让人们喜欢的好作品,有学术价值的作品; 2.要有雄厚的理论支撑。要有一支理论研究队伍,有学术高度,要把画家的理念、成就梳理出学术体系、学术思想做为理论支撑。 3.要有雄厚的财富支撑。 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的力量,能代表国家形象的艺术作品进行推动,包装,现在我们一盘散沙,我们只是在完成一个工作而已,而不是真正的文化战略,还没有上升到一种文化输出应该有的状态,这个状况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在20世纪初,全球的艺术中心从法国的巴黎转移到了纽约?这个现象说明必须有国家的专业队伍进行研究。说明美国在文化的输出是有手段和战略的,它就是运用两个杠杆,第一,雄厚的理论支撑,哲学的,观念的。第二,雄厚的融金支持,它有许多艺术基金会。 中国有很多富豪,如果他们能够对文化支持,投入文化基金,支持我们这些国家的政策文化输出的话,应该有免税政策,我们现在仍然在文化的投入上没有税收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鼓励企业投入文化上来,这就叫杠杆,看起来是从一个点进去,可以撬动整个地球,所以说整体上的文化就会被撬动起来,兴趣也就会投入到这里面来。就是要推出中国的大师,中国的天价,没有天价是惊动不了世界的。我们出去搞一个展览,应该像外国的大师展览一样,你的整个文化的背景资料,艺术成就,所有的系统记录,你的整体的包装设计,展览的形式,配框,框子的包装,运输,保险等等这些是专业化的,还有整个展览衍生产品的跟随,纪念品,当然还有广告的宣传,都得有大量资金的投入,人家才可能意识到和参与你的代表中国文化形象的展览,才会崇敬你。不然的话,我们搞一个展览一窝蜂的上去,只有一个前言没有研讨会,没有学术支撑,没有论坛,没有学术主张,没有学术思想,不知道你要画什么?今天的展览和明天的展览差不多,这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中国不是没有好东西,中国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发这些年来,中国的艺术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的绘画成就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完全是能够把中国的好东西推出去的,但是我们缺少团队,缺少权威。所以想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是需要有一个战略研究,需要一整套国家战略的。 代表作品
秋冥 203x151cm 绢本设色 1991年
十九秋 110x170cm 绢本设色 1984年
米脂的婆姨 230x80cm 绢本设色 1985年
山地 136x166cm 纸本设色 1983年
清明 127x177cm 绢本设色 1985年
夏 127x191cm 绢本设色 1985年
街道主任 112x91cm 绢本设色 1981年
酸葡萄 175x245cm 绢本设色 1988年
魂系马嵬(与高云合作) 160x191cm 纸本设色 1989年
孤叶 185x104cm 绢本设色 1990年
红苹果 114x80cm 绢本设色 1990年
朝露桑 200x148cm 绢本设色 1992年
落英 90.5x350cm 绢本设色 1992年
初春 100x66cm 绢本设色 1993年
秋韵 96x75cm 纸本设色 1993年
绣女 90x70cm 绢本设色 1995年
韩国留学生 130x60cm 绢本设色 1998年
幽谷 160x80cm 纸本设色 2002年
日本女孩 65x50cm 绢本设色 2014年
偏梳苗妇女136x69cm 纸本设色小图 2016年
大凉山的女人 64.5×57cm纸本设色 2015年
百合依依 56×89cm 纸本设色 2015年
毛泽东词意 142×197cm 2015年
杨开慧 102x165cm 2011年
余韵 189x115cm 纸本设色 2009年
胜利女神 214X132cm 纸本设色 2008年
丹巴丽人 160X70cm 纸本设色 2007年
孙中山在天津 216X105cm 2004年
澳门中学生 180x95cm 纸本设色 2001年 |
相关阅读:
·舒勇每日一画“一起向未来” 让冰墩墩、雪容融带你读懂中国 2022-02-16
·陈东升:中国经济的三大变化 2022-02-12
·习近平谈“虎” 2022-02-10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 2022-01-05
·中国文创元浦团队跨年巨献(九) | 曾军文化文学研究专辑:新中国初 2022-01-05